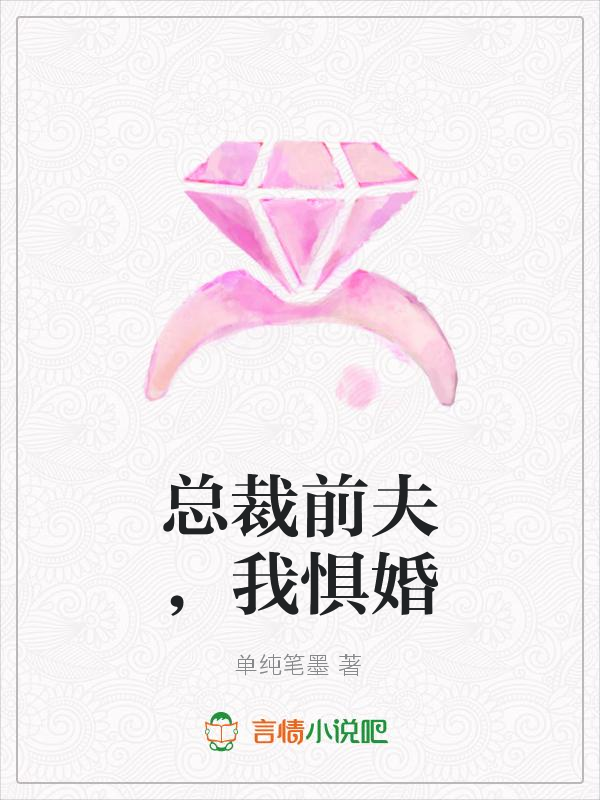晨曦微光映过窗纸,洒进屋来。
梁缨闭着眼翻了个身,想再眯一觉,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浓浓药味儿随着凉风窜入鼻中。
“缨儿,快起床,把这药给喝了。”李蔓榕放下手中药碗,走过床边轻轻推了推她。
梁缨迷迷糊糊睁眼,伸了个懒腰,坐起身:“娘,这大清早的,喝什么药啊?”
李蔓榕淡笑,端起桌上的药碗,坐在床边,吹了吹:“这是娘一大早就到药铺去抓的祛毒的药,熬了一个时辰呢,快喝了。”
“祛毒的药?娘,我又没中毒,为何要喝这药?”梁缨不解。
李蔓榕嗔了她一眼:“那狼牙狼爪子上指不定有什么秽物呢,若被挠了,伤口可是会溃烂下去,甭管你现在有没有受伤,吃了这药,都没坏处。”
梁缨望着碗里黑乎乎的汤碗,心知拒绝不了,索性眼一闭,端过碗,“咕咚”两声饮下。
李蔓榕欣笑,接过药碗,拿帕子为她拭去嘴角药渍,坐在床边轻叹一声:“缨儿,你跟娘说,你怎么会和王爷去了南山,又怎么会一同掉落那悬崖下了呢?”
口中苦涩蔓延,梁缨靠在床边,面容疲惫:“娘,昨夜的事……我已经忘了。”
“忘了也好。”李蔓榕攒眉叹息:“娘只是不想让你被外人嚼了舌根。”
“他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心中坦荡,还怕他们说什么不成。”梁缨直起身,眸中隐怒。
这淮安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若是有个风吹草动,不出一日,便能从城东传到城西去。
昨夜那般折腾下来,怕是吵醒了不少左邻右舍的好事之人。
李蔓榕望着她,眉心一阵跳动,亦是为她心忧:“你不去看看九王吗?他貌似伤的很重,也不知是何人派来的刺客,下手如此狠毒。”
靠着床边的身子陡然僵硬,梁缨心烦意乱闭上双眼。
见那秀容疲惫,李蔓榕无奈叹出一口气,扶她躺下:“先歇着吧,莫要再胡思乱想伤了身体。”
房门被轻轻扣上,梁缨缓缓睁眼,摸出绣枕下的素纸,一行浓墨润湿了双眼。
吾爱梁缨慧鉴:
顷诵华笺,具悉一切。
家母突患疾病,你我之约恐要食言,但请缨儿放心,待母体康,我定登府提亲,履行你我之约,望缨儿见谅。
韩世忠笔。
这信是昨日怀月送到她房中来的,等了这么多日,终是有了他的音讯,虽然心中已安定下来,却是说不出的失落。
她苦笑着闭上眼,全然没了睡意。
宁贵一夜未敢合眼,这会儿见床上之人动了动身子,忙上前查看:“主子,是伤口又疼了吗?”
床上之人薄唇紧呡,身子微微颤抖,似是忍痛。
宁贵仍是有些不放心,皱眉道:“这药是下的有些猛了,主子若是受不住,老奴便让那郎中把药给换了。”
“这点儿疼痛算不得什么,比起那人的鞭子,差得远了。”苍白的嘴角一笑,那抹未达眼底的笑意,却冰冷如霜。
宁贵垂首,心似被针尖扎了一下,疼痛酸楚。
那是一年的元宵佳节之夜,永安亭中张灯结彩,歌舞琴乐声似要把满湖凌冰融化。
这,也是那个小小的人儿,渴望已久的欢容,因为只有此时,他才能无所顾忌去望那高高在上的父皇,渴取他一眼的回顾与笑容,便已心满意足。
只是这祈盼与欢笑,却在那一夜,成为他永生不愿再回首的往事。
宁贵想的出了神,连床上赵构的呼唤都未听见,猛然惊觉回过神来,忙垂首俯身:“主子是饿了吗?老奴这就去叫人备些吃的。”
“罢了。”见他恍惚,赵构皱眉摆手,缓缓坐起身来:“她怎么样了?”
“主子是在担心梁姑娘?”
见他不语,宁贵垂眉:“只受了些皮外伤。”
“那就好。”想起昨夜那女子为了他的伤,竟可不顾男女有别之礼,与恶狼交斗一幕,更让他不能相信她是这将军府的千金。
他突然觉得事情变得有趣了,冰冷的双唇不自觉泛起一抹笑容。
“王爷不觉得这么做……很是冒险?”
“你怀疑那些刺客是本王派来的?”寒眸微眯。
宁贵忙垂首:“老奴不敢。”
赵构冷哼一声:“本王还犯不着这么做,你看不出那些人要置我于死地吗?”
宁贵垂首,当时他被两人缠住,无暇顾及其他,自是不知王爷受了伤。
见他神色恍惚,赵构心中冷笑,凝眉沉声:“你知道本王在那崖下,所以故意拖延时间,下山去带了梁家人来此?”
“老奴该死!”宁贵曲膝一跪:“是老奴会错了主子的意思。”
他当时在崖边捡到了主子身上的玉佩,便朝那崖下呼喊了两声,听不到回音,见那悬崖其实是个石坡并不深,且以主子的武功应是无事,遂怕打扰了崖下的良辰美景,索性跑下山去带了梁家人来。
见地上之人如此坦然,赵构白了脸:“蠢才!本王差点儿就被你害死!”
“老奴甘愿受罚。”
伤口又在隐隐作痛,赵构喘出一口,闭上眼:“出去吧,本王累了。”
“是。”宁贵垂头,取出袖中玉佩,轻轻放在床边,退了出去。
长指抚过温润白玉,祥云结上染了滴滴血迹,握着玉佩的指尖惨白,似那年永安亭边少年惨白的双唇。
 连载中
连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