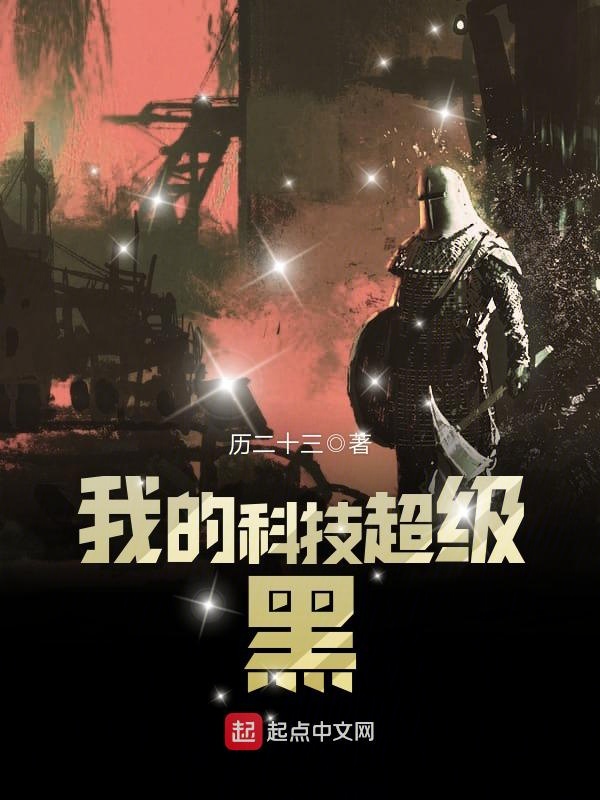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穿越者的无名日记》第九章 暴雨到来,杀戮开始 免费试读
神历1467年 8月17日天气:大雨
我的身体在不停地颤抖,因为我这炮轰出去是要死人的。长这么大我连鸡都没有杀过一只,更别说杀人了。虽然我以前打架,还把人打进了医院,可是当时我也被吓得不轻。
我本以为,我已经准备好了,但是一想到只要我一扣下**,刚刚还在活蹦乱跳的人就会成为一具尸体,我的心里就很犹豫。我在心里怒吼:犹豫个屁啊,在不扣下**,等他们冲过来了,我们都得死。
可是我的手指就是不动,只要在往下扳一点,RPG就会发射。
“***,给我扳下去。”我嘶哑地怒吼道,我感觉到我的太阳穴在跳动,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去扣动**,可是我的右手食指就是不动!RPG不像魔法,魔法只要成功释放了,只要你一个念头就会主动去攻击敌人,不会给你身体反应的机会。
我前方的黑袍面具人已经毫无阻碍的接近了快三百米了,他们离我们的直线距离最多只有二百五十米了。菲奥看出了我的异常,不如说她早就知道我这边会出问题早就做好了出击的准备,可是面前至少也有三十个黑袍面具人,她冲过去只能被他们剁成肉泥!
可是她还是冲了出去,从我旁边冲了出去,我感受到了她的冲刺带起的风,是那么的决绝,是那么的……义无反顾!
压抑了很久的大雨终于降临了,有些雨水划过空气打在地面的泥土上,有些打在树叶和小草上,还有些打在我前方那身穿银白色铠甲的骑士义的身上。
我看着冲出去的菲奥,我的心在发出怒吼:扣下**,不要等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一股热气冲上了脑门,我再一次发出怒吼,好像有什么东西帮我扣动了停在**前的手指,我见一声巨响,那是炮弹离开炮膛的声音,我看见炮弹喷射出的白色烟雾,我看见炮弹在菲奥之前落入了敌阵的中心,炸开,就像一朵怒放的花朵。
黑袍面具人虽然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但是任然有一部分被火箭弹炸伤,运气好在爆炸边缘的,被火箭弹的气浪掀翻,运气不好的,在爆炸的正中心,就算有斗气防御也被四散的弹片伤的不轻。菲奥也被气浪波及到了,不过问题不大,只是冲刺的速度被减慢了。
雨滴落在我的身上,将我身上的衣物打湿,雨水落到炮筒上,炮筒发出“嘶嘶”声,冒出浓浓的白雾。风从我耳边吹过,带来了丝丝凉意。
我的脑中一片空白,站在原地看着再次冲来的黑袍面具人。看着菲奥上前迎敌,也看躺在地上哀嚎的敌人,看着那些挂在树上破碎的肢体,我并没呕吐只是单纯的站在一旁看着。
我右手一松,扛在肩上的火箭筒“哐当”一声落在了地上。三柄长剑将我护在中间,也有三柄长剑将艾蕾拉护在中间。我回头看去,发现云溯晴双手正挥舞着手中的长剑在人群中厮杀,另外四把长剑在人群中飞舞。
这次袭来的黑袍面具人实力不强,但战斗经验丰富,知道无法突破防御立场的守护,分出一部分人牵制住菲奥和云溯晴,其他人将我和艾蕾拉围住,不停的攻击。他们并没有想对菲奥和云溯晴下杀手,而是试着活她们,来逼我们自己走出防御立场。
耳边传来艾蕾拉的哭泣声,艾蕾拉知道今天的死局已成,没有一丝生机。在绝望面前就算艾蕾拉再怎么坚强,也会哭出来。看着哭泣的艾蕾拉,泪水从她红红的眼眶里流出,耳边不时传来黑袍面具人攻击防御力场的声音。
记得昨天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看到一群人正在欺负一个白头发的小孩,白头发的小孩并没有反抗,就只是坐在地上哭,好像在等其他人来帮他一样,可是没有人来帮他,周围的人也只是变本加厉地欺负他。
我终于看不过去了,走过去用一种跟自己完全不同的的语气说:“不就是被人欺负了吗,什么好哭的,把他们都杀掉不就没有人欺负你了吗?”语气中充满了寒意,听这个声音仿佛让人置身于凛冽的寒风之中,还带着浓浓的杀意,好像要杀掉整个世界一样。我被我自己的语气吓到了,从梦中惊醒,醒来后发现冷汗打湿了整个上衣。
不知道为什么,看见哭泣的艾蕾拉会让我想起了那个梦。好像艾蕾拉就是那个哭泣的白发小孩一样,而我也用和梦中一样的语气重复了一次梦中的话。
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吊坠中取出吊坠中取出来两把黝黑的乌兹***,卸下弹匣开始一枚一枚地往弹夹里装着子弹,装弹的速度不快,不过装填每一枚子弹所用的时间都一摸一样。
不一会我就装满了两个弹夹六十四发九毫米子弹,然后我又从吊坠中取出了十枚***和一把弹夹容量九发,装满0.44英寸马格努姆手枪弹的沙漠之鹰,我蹲在地上把它们整齐得摆放在我们面前。
我将沙漠之鹰手枪插入腰间,取出一根绳子穿过拉环,将***绑在一起,然后拉开其中一颗***的保险栓,在数到三的时候,迅速地将这一捆***扔出去。
防御立场外的黑袍面具人们似乎并没有警戒这个被我投掷出去的东西,他们还在不停的攻击着防御力场,菲奥在艰难的抵挡着他们的攻击,看上去最多还有三分钟就会被他们抓住。云溯晴的四柄飞剑也被他们缠住,而她也在被无名黑袍面具人围攻,险象环生。
一秒钟的时间够做什么?对于普通人来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够,对于那些强的离谱的人在说这一秒可以做很多事情,对于我来说足够让这捆*****并爆炸。
*****,发出清脆的响声,紧接着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爆炸的气浪携带着尘土和弹片狠狠地刺进这群毫无防备的人身体里,在他们身上开出一朵朵深可见骨的血色花朵。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我没有任何不适,也没有任何反应。
等着爆炸的气浪结束了,我慢慢地走出防御力场,就像走进宴会的绅士一样,而我双手中的乌兹喷吐着火舌,将九毫米的黄铜子弹一颗一颗打进他们体内,就像我送给举办这次宴会的主人的礼物一样。
我用双手中的乌兹***做着有规律的点射,如果是扫射的话,六十四发九毫米子弹,以乌兹***的射速最多两秒就会把弹匣打空。而且斗气防御也不是纸糊的,中远距离平均十发九毫米子弹才能贯穿他们的防御,近距离只需要五发。
挺过还活着的黑袍面具人还有三十三人,云溯晴那有十人,菲奥那边有三人,剩下二十在我这边,在刚刚的爆炸中,有十个死去或是失去战斗力,在出去我趁他们在爆炸后没反应过来杀掉的三人,现在我需要面对的只有七人。
九发马格努姆手枪弹加上三十九发九毫米子弹,七个人足够了,不过要是把其他十三个人算进去的话这些弹药还不够,必须节约着用。
七个黑袍面具人决定一起向我发起进攻,他们从不同的方向攻了过来,而我只有两只手不可能同时向他们开枪,这样一个他们以为的死局就形成了。
可是这个死局有一个成立条件,那就是——我呆在原地防御。但是现在对于我而言,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
我随意选定了一个方向,双手拿着乌兹***向着那个方向射击,而我自己也在向那个方向冲去。手中的乌兹***发出轰鸣,面前的黑袍面具人的眉心处出现了一个孔洞,面具也裂开了露出了面具下的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
我的脸上毫无表情,双手分开指向左右两方,扣下**,子弹想长了眼睛一样钻进他们的心脏。还剩四个人,还剩二十四发九毫米子弹。
我机械性的开枪,躲避,然后在开枪,动作行云流水,宛如一台杀人机器一般。在五分钟后剩余的四个黑袍面具人全灭,我的左手也中了一刀,不过匕首上并没有淬毒,但是左臂现在已经完全被麻痹了,麻醉感还在想身体四周扩散,估计他们的匕首上抹了麻药。
我用右手迅速地拔出了插在腰间的**,这时麻醉感已经开始影响我的视觉了,视野开始模糊,有些看不清眼前的东西,这样的话就不能瞄准了。不过如果是在零距离的情况下开枪的话,那瞄准也就不需要了。
我向围攻云溯晴的五人冲了过去,他们发现我冲了过去,立即分离出一人来牵制我。他们五个人配合的很好,所以才能拖住云溯晴,但是分出了一人后他们的配合不再完美,原本平稳的战局被打破了。
缺少一人的他们,现在只能勉强在云溯晴的攻势下坚持。原来守护我的三柄剑,现在正守护着斗气和体力都完全耗尽的菲奥,不然现在他们已经完全输了。
我看着向我冲过来的敌人,我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神冰冷,脑中在计算着开枪的时机,他可能躲避的路线还有我接下来的应对方案。
他投掷出左手的匕首,右手的匕首反握在胸前。
我咬着舌尖让自己保持着清醒,看着飞来的匕首,我不退反进,在要被击中的时候,猛的停住。以右脚为轴心旋转,让匕首击中已经麻木的左臂,左脚狠狠地踏在地上抵消着匕首的冲击力。而这时敌人也已经到我身前了,原本反握在胸前的匕首,现在高举着向我的头刺来。
因为我将左臂对向他,他看不见我拿着枪的右手的动作,所以他没发现枪口,我的左臂还有他已经在一条直线上了!我全力挪了挪左臂,不管有没有挪开,我右手已经扣下了**。
撞针击打在0.44英寸马格努姆手枪弹的底部,火药爆发的冲击力将弹头送出枪口,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巨大的后座力将我的持枪的右手向后后推去,我的右手也被巨大的后座力震得发麻。
弹头旋转着前进,划破空气,穿过雨滴,从我的左臂擦过。左臂上方的皮肤和肌肉被撕碎,留下了一道深可见过伤痕。弹道也发生了改变,原本笔直向前的子弹,向上偏离,黑袍面具人的身体出现在弹头前方。
我看着他的匕首向我刺来,我的脸颊已经出现了一股微痒感,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一样。其实是他的匕首已经接触到了我的脸颊,但是匕首再也没有可能前进分毫,因为子弹携带着巨大的动能击中了黑袍面具人,撕裂了他的心脏,巨大的动能将他击退,匕首也远离了我的脸颊。
温热的血液从他的胸腔里喷涌而出,一些溅在了泥泞的地上,一些溅在了高大的树上,更多的喷射在我冰冷的脸上。我的表情没有因为这些血发生任何变化,不知道是敌人还是自己的血混着泥浆雨水沾满了我白色的实验服,丝毫看不出来这个人在一刻钟前还因为怕杀人而无法扣下**。
我没有停留继续向云溯晴那方的战场走去,跨过脚下的尸体,踩着混着血液的泥浆,向前走去,就像一尊行走在战场上的魔神。
我举枪然后扣下**,中间没有任何瞄准的动作,因为敌人就在我前方不到两米的距离。雨水打在我沾满鲜血的脸上,敌人的鲜血也这样打在我的脸上,围攻云溯晴的敌人已经全灭了,现在还剩八个黑袍面具人,我还有五发0.44英寸马格努姆手枪弹。
就在我准备继续解决剩下的敌人时,云溯晴伸手拦住了我,我用冰冷眼神看着她,她也用冰冷的眼神看着我。现在我们两个就像两块碰在一起的冰山一样,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的视野变得更加模糊了,就连云溯晴的脸也看不清了,麻药的效果彻底爆发了。我的身体向前倒去,右手握着的沙漠之鹰也掉在了地上。不过我并没有倒在地上,虽然被麻醉了,我依旧感觉到了,我没有倒在地上而是倒在了某个人温暖的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