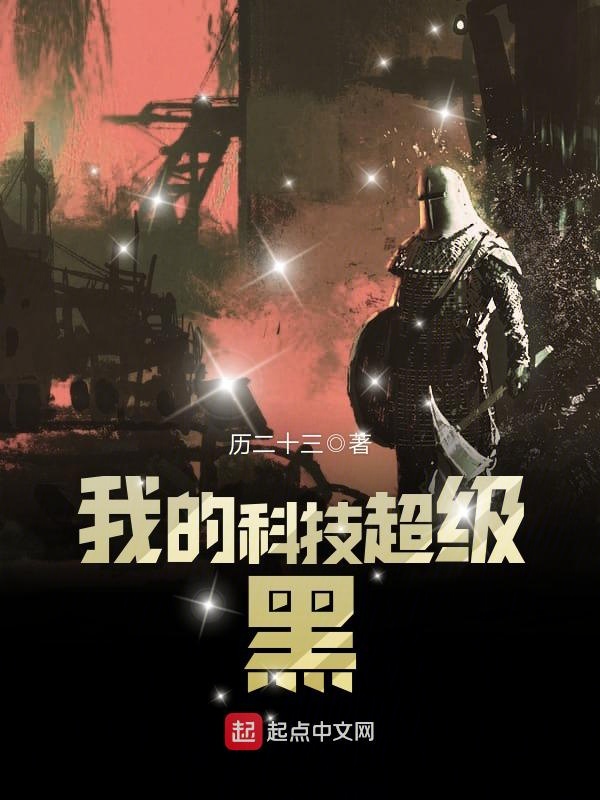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庶后嫡谋》第十章:南鹊山寺 免费试读
没有车马,我便只好徒步上路,又担心在天亮之前无法赶到南鹊山寺,故走得急促。脚下的利草枯枝将裙摆划得有些破烂,但好歹未像那天晚上,将腿脚划伤。
南鹊山寺离阿婆的住处不远,都是在京郊。我走到南鹊山山脚时,已近子时,约莫一刻钟,我才走到山寺所在的半山腰。此时我已筋疲力尽,抬手轻扣了下寺门,又怕力气太小寺里守夜的僧人听不见,遂握拳再敲了三下。
不多时,我便听见寺里有悉悉索索的脚步声,像是脚踩枯叶发出的声响。寺门稍开了缝隙,一个约莫十二三岁的小僧人探头出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小师傅,我是……”
“可是承阳公主?”我话未说尽,那小僧人就率先开口。
“是我。”
“快进来,”那小僧人将我领进寺中,边行边道,“公主此行凶险万分,王后甚是担忧,眼下公主回来了,王后见着公主平安,定是十分欢喜。”
那小僧人边走边说,也不知是在对我说,还是在自言自语。
他比我矮一个头,倒是清瘦,只是步履匆匆,怕赶不上什么大事似的,一步不歇。
“越朝尽灭,你大可不必避讳越王室,唤我越西即可。”我道。不论是温意慈还是见着我的任何越朝旧人,我都不愿他们唤我“承阳”,我下意识地排斥这个称谓,就像排斥父王的承阳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我身在一团泥沼之中,逃脱不了,更无法脱身。
“贫僧是陈国人,曾居陈越边界九江郡,七年前陈越之战陈国大败,贫僧随家父家母北迁,逃难到越国。家父家母北迁途中病逝,贫僧幸被世子王后收留,原本是在京都安居的,前几日****,这才随王后来到南鹊山寺,做了守夜和尚,”那小僧人如是说,“贫僧并非避讳越王室,贫僧只是感激王后救命之恩,只崇敬之意。望公主莫要见怪。”
我瞧这小僧人不过十二三岁的年纪,行事谈吐却都十分沉稳,与一般的孩子截然不同。心下暗生疑虑,莫非又是母亲早前埋下的一颗棋子?复又想起他方才忧心忡忡的样子,遂打消了这念头。这南鹊山寺是眼下越国唯一一处隐世之所,是棋子也好,不是棋子也罢,我只是希望再不牵涉任何无辜人。
他送我到水居门前便止步了,走时只双手合十,微微躬身,道了声“阿弥陀佛”,随即转身离开。
我推门进院,见素白纱窗仍有熹微烛光。我小时候常生病,夜里常常因病痛哭闹,每每如此,母亲都点盏烛灯在床前案上,为我守夜。
院里十分清冷,原本便是在深冬,院里的梧桐老树连零星的叶子也没有,枯枝空挂,在此刻看来,竟有几分荒凉的味道。
我推门进屋,母亲闭目和衣倚在床案,案上点了一盏烛灯,光有些暗。听见动静,母亲睁开眼,见着是我来了,缓缓起身。
“我让卜芥和儿茶准备热水,你先洗洗风尘。”母亲的声音又轻又淡,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半夜突然来访,母亲倒未显得惊讶。母亲原本就有头疼的隐疾,夜里若有安神香定然是天微暗时就要休息的,若不然到后半夜头疼发作,怕是一夜都不得安生。母亲到子时还未休息,大概是这几夜都在候着我。
“母亲……”我不知如何开口,千言万语像是如鲠在喉,我想扑在母亲放声大哭,像小时候被不懂事的妃嫔欺负了关在小柴房一整晚,像背不出繁复的文章在夫子那里受了委屈。
我抬手抱住母亲,母亲有些微愣,但随即也抬手轻轻抱住我。
母亲清瘦了太多。耳边的白发丛生,沧桑顿显。我一直以为母亲是从前撑着一身锦衣华服,高束珠络后冠的模样,手轻轻一抬,偌大的袖口就能将我遮住挡在身后。
母亲老了,双眼里的无奈太多太多了。我已经许久不曾在她跟前流泪了。
京都的这几个月里,我的脑子一片混沌,连疼痛都有些麻木了,连夜奔波也不觉累。
此时在山寺水居,倒觉得疲惫非常。
母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又走出门外唤人为我端来热水,供我梳洗。
母亲为我腾出了一间房来,在山寺的北边临门处,而水居却是在南边。我与母亲许久未见,此间又发生了许多事情,我想与母亲说说话,像从前在长乐殿那样,但凡受了委屈,总是要和母亲同寝。
我刚露出些不情愿,母亲便态度坚决地要我去北边竹居,我见母亲稍显疲惫的神情,料想母亲或许是头疼发作怕被打扰而无法安眠,又或是怕我担心,遂犹豫了片刻,也就随儿茶走了。
我独坐在浴盆里,四周静得很,仿佛能听见落叶的声音。我轻合双目,觉得累极了。
京都内有多处庙堂,而南鹊山寺地处京郊,因此香火并不旺盛。后因母亲的头疼隐疾,需僧人诵念经文缓解,又不想消息露出宫外,遂找了京郊的一处偏远山寺,将香火彻底垄断,由越王室供养。想来已有八九载,这处山寺怕是鲜有人知了。
我梳洗完毕,将里衣松松垮垮地绑在身上,回头将李清给我的匕首放在床案上,熄烛就寝。
今夜无月,屋里暗得很,我仰面躺在床榻上,觉得心安。
还未沉睡,我就闻到一股熟悉地血腥味。刚要沉睡的记忆一下子涌到我眼前,脑中眼中,全是长乐殿的尸横遍野,京都市集的血流成河。
我的身体止不住地发颤,直至听见窗扉开动的声响,是有人侵入屋内,才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悄悄拔起未紧合的匕首。
我轻轻地走下床榻,借着床帏的位置找到墙角的方向,又顺着墙壁寻着记忆中的方向往门那边走。
那人自进屋后边再没声息,若不是屋中始终弥漫着淡淡地血腥味,我根本不会知道有人侵入屋中。
我左手撑着墙壁,右手紧握匕首,走得极缓,怕稍错一步,就与那人正面相交。
我寻到门的方向,刚靠近屋门,却又突然听见院中有异响,像是人轻微的脚步声。我依着这声音判断,院中绝不止一人。这些人脚步轻盈,倒不像受伤的样子,方才那人似乎是被这些人追杀着逃到此处的。
我顿时分不清敌友。竹居临门,那人逃到此处,要么是不熟悉地形环境误入,要么是受伤太重,已撑不了太久。
院中那些人似乎还在四处找寻着,但又迟迟不肯进屋来。母亲虽在水居,可水居距离竹居也不到半里,我担心那些人会找到母亲或者其他僧人那里,若这些人起了杀心,不论母亲还是寺中的僧人,都绝无招架之力。我便想着弄出些声响,从侧窗逃出,往后山上去。我在山寺修行一年,对于周围环境算是熟悉,后山灌木丛生,阡陌交错,那些人若是进到灌木林中,也要绕些时候。
我这么想着,右手握了握匕首,顺着墙壁找到侧窗,刚摸到窗棂准备打开窗户,手腕便被人握住,同时,那人怕我惊叫,也用手将我的口鼻捂住。
那人十分高大,我被困在他胸前动弹不得。鼻子被捂住使我呼吸困难,那人感觉到我的极力挣扎才微微松开手,好让我呼吸。
那人身上的血腥味十分浓重,我感觉到耳边**,似乎是他胸口的上口溢出了血。
院中的那些人仍未离开,或许他们知道这人就在附近,因此不肯离开,而或许那些人又十分害怕这人的功夫,因此迟迟不敢进屋来。
院中那些人步履轻盈,声息也十分轻微,就算是哥哥营中精骑队的那些人,恐怕也做不到。而他们竟然因惧怕这人的力量不敢贸然进屋来,此人又是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我的头皮阵阵发麻,再不敢动弹。
那人站在我身后一动不动,我不知该如何是好,右手的匕首仍握得紧,那些人仍旧在院中徘徊。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我想,他本就伤重,或许我可以反手将这人刺伤,令他无法动弹,再从侧窗逃出,将院中的人诱往后山。
握紧匕首的右手颤了颤,我刚想抬手,屋子左边突然传来声响。那些人应声而动,很快就离开了。
我松了一口气,身后那人突然动了动,我立马又紧张起来,却听那人似乎是撑不起身子了,一下子跪伏在地上。
我惊了一下,立马跳开,又疾步走到床案前想要点灯,刚将烛心引燃,就见那人撑起身子一手拂开烛檠。烛檠落在地上,发出尖利的嘶鸣,划得很远,火苗闪烁了几下,就彻底熄灭了。
我呆愣住了,手还半抬着,一下不知该做何反应,屋里一下子又变成伸手不见五指的样子来。
我突然想到,方才那解围之人确确实实是从寺里出去的,而他后山去,应是知道山寺周围的地势的。
屋里这人或在寺中埋伏了人手,而南鹊山寺的香火早已被母亲垄断,鲜少有人知道京郊有这样一个极其偏远的山寺。
这人大概是与母亲有些关系,方才又抬手拂倒烛檠,显然不想露出真容,或许身份也不简单。
“去打点水,找些纱布,我要清理伤口。”那人声音极低,像是哑了嗓子。
我犹豫了一下,又俯身要去捡烛檠。还未碰到,那人便又握住我的手腕,这次稍用了力,我有些吃痛。
“没有光,我看不见。”我说。
那人还是没有松开手,却毫不客气的将烛檠踢远了些。
我悄悄吸了口气,就算这人与母亲有关,但看他这么不客气,虽然不会要了我的命,可让我缺胳膊少腿儿就不一定了。
我起身又按着方才的方法,顺着墙找到木门,出门打水去了。外头没有屋里重叠交错的帷幔,倒是亮堂一些。我犹豫着要不要告诉母亲,随即又打消了这念头。母亲若是知道今夜有人闯入,不会拿我冒险,更不会让我住到竹居,那些人最易侵入的居所。
母亲的心思越发深沉,我不知道她在离宫前埋了多少暗线,又有多少人正牵扯其中。
我端着一盆水拿着纱布回来时,那人正倚在床边,些许微光从敞开的木门透进屋里,他手里银光微泛,那是银白刀身。
我将水和纱布放在桌上,又怕他嫌这冬夜的水太凉,遂有些犹豫。
那人听到动静便撑着坐到桌前。我听到衣襟撕裂的声音。
那人三下两下便快速清理了伤口,似乎是不想再多待片刻。
见他清理完伤口快步就要走出门,我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却见他顿住,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丢了个东西来,摔在桌上,声音清脆,像是玉石。
“拿它来求我,承你救命之恩。”他说。
说罢,转身就消失在夜幕中。
我呆愣了片刻,才摸索着捡起烛台,灯光一亮,屋子里便敞亮了。桌上有许多带血的纱布,铜盆里全是血水。想来那人伤得不轻。
桌上多了块碎玉石头,我拿起来瞧了瞧,上面磨痕太多,像是被人从某个乱石堆的淘出来的,早不复光泽。
那人让我拿这碎玉石头去求他,应是知晓我的身份。那人大概也是眼下盘根错节势力的一支吧。
外头天还黑着,我担心被引到后山的那群人找不到那人又要回来,遂始终不敢入睡安眠,好在等到卯时已过,那群人没再回来,我便也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本书由潇湘书院首发,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