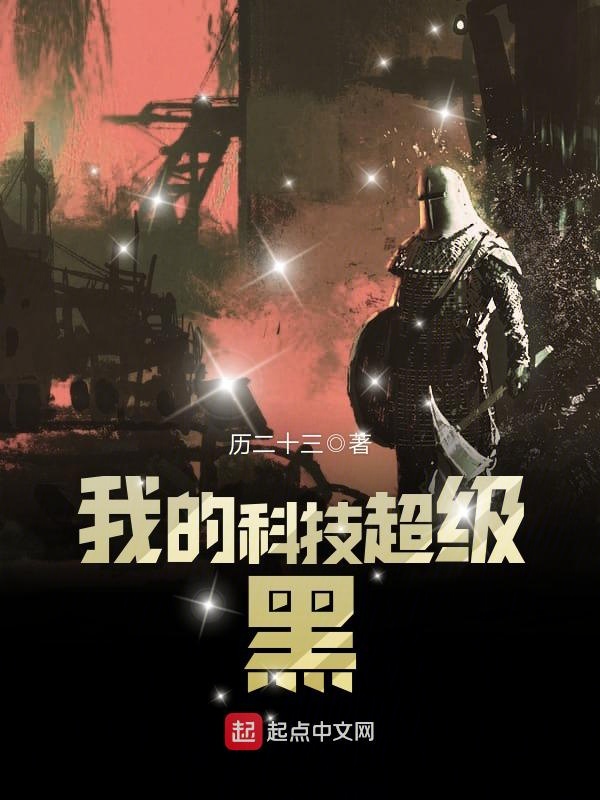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庶后嫡谋》第十六章:今非昨 免费试读
这一觉睡得很沉,难得没有扰梦的人和事。醒来时光很昏暗,重重的红粉帐幔将光一层一层地剥离开,让我有些恍惚。
胸腔很闷,像有千斤重担压在上面,让我无法呼吸。我艰难地喘息起来,胸腔里似乎被什么东西堵塞了,我开始咳嗽。
外面有人似乎听到了我的声音,推门进来,他绕过屏风,掀起帷幔正要走到我面前。我突然呛出一口血来,接着是第二口、第三口,我没能看清他的模样。
那人快步走到我床前,将我扶起靠在他胸前,又拿起床边桌案上的锦帕来拭我嘴角的血。我见锦帕上还有未干的血迹,想来我在昏睡时也呛出过血。
我还未缓过神来,胸腔上的挤压却越发严重,脑中混沌不堪,无边的困倦凶猛地涌来。我再次昏睡过去。
再醒来时帷幔已被撩开,有宫人在一旁候着,见我醒来又慌忙出殿去,不多时,毕安便带着太医来了。
“越姑娘已无大碍,只是积郁成疾,需得静养。”
“这段时间就烦请张太医照顾越西了……”
毕安和那位张太医还在屏风后面说着什么。我转过头,那桌案上放了一只素白的瓷瓶,染血的锦帕已经不见了。
那位张太医走了,毕安从屏风后面绕过来。
“醒了?”毕安上前轻声问。
“嗯,麻烦公公了。”我答。
“醒了就好生养着。”毕安又说了些宽慰的话,嘱咐了身边的宫人几句,转身想要离开。
“我方才醒过来时,可是谁来过?”我问。
毕安顿了顿,转过身来,“方才是我叫了宫人来,你突然呛血可把人吓坏了。”
我默了一默,“多谢公公了。”
毕安点了点头,看着我似乎还想说什么,稍停了停还是转身走了。
说到底,我现在也只是个宫人,万万轮不到要别的宫人来侍候我,许是毕安为还我的恩,才对我上心许多。
傍晚,来送食的还是毕安。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宫女要世子身边的近侍来侍候,的确是逾越了。
我思度再三,还是问了毕安,“公公可否告诉越西,子义的生路可是林家的死路?”
毕安默了默,最终还是摇了摇头,只道:“一切都是殿下的旨意。”
我终于沉默了,心沉得很深。我原以为他是念着旧情的,纵然是他逼不得已,屈身在长乐殿做了我七年侍婢,我总归是将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如今想来,他是记着那七年屈辱了,子义生,林家则死,他从来没有什么恩赐,只是交换罢了,总得有人流尽血和泪来偿还他那七年的屈辱。
我胸口又一阵闷疼,下意识地捂住胸口,毕安见状赶忙来扶我。
“殿下是因着你给了那孩子一条生路,你若是没了,那孩子的生路也就断了!”
胸口揪心地痛,那最后一念也终于没了。“他是拿子义来逼我么?!”
在确认他并非顾念旧情后,我开始对他所有的行为恶意揣测起来。是了,我逼着他做了我七年侍婢,而母亲则将那容华夫人给毒死了,我虽不知道容华夫人和他是何种亲密关系,但从那次兰芷殿的窥探,我知道容华夫人对他很重要。
他放任母亲和我的所有动作,是想留了活口慢慢折磨么?是了,他没有加害我和母亲,没有将我发配军营,哪个宫女能有这般殊遇,让其他宫人小心侍候着,太医鞍前马后地照顾着?
可是我还要这般苟活着,因为子义要活着,林家要活着。
我想我是有些癫狂了,我在毕安惊愕的眼神里,慢慢笑了起来,像七年前的样子。
无尽的绝望像黑色烟雾一样,沉重又严实地将我笼罩起来。毕安说我的路还很长,可他却没有告诉我,那条路是无望的。
我想起母亲离宫的那天,她彻底弃我而去,独独将我一人留在越宫的那天。我衣袍不整,发髻凌乱,甚至连鞋子都没来得及穿,赤着脚从长乐殿跑出来。天才微微亮,宫里出奇的静,母亲的车马在远远地城门那边,渐渐缩小成一个仿佛梦中追不上的影子。我跌在雪地里歇斯底里地哭喊,直至嗓子沙哑出血。
那是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宫人们说这是瑞雪,今年的好兆头。
而无一例外地,父王在哪个妃嫔的内殿里,整夜笙歌,宿醉未醒。
“公…越西你好生休养,待身子好些了,再去服侍殿下。”毕安有些担心的样子。
“不必了,公公尽管安排便是,奴婢总得尽心些,才对得起殿下的恩典。”我想我是笑得很好,连毕安都呆愣了一会儿。
“这…奴才…我,我这就去安排。”毕安回过神来,像是被什么吓着了,说了几句话就匆忙离开了。
殿门关了,殿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红粉帐幔仍旧将光挡在外边,殿里的光仍旧很暗,像是要藏住谁的身影。
我呆愣了很久,心绪繁乱,什么都在心里,又似乎什么都不在心里,空荡荡的,有些冷。
约莫在殿里待了三天,宫人们和前来问诊的太医都意外地客气,他们似乎都认定了我和陈国世子有着某种关系。
林岑的尸首被阿泽火化了带去毗岵山,哥哥就葬在那里。我无法想象阿泽一根一根拔出穿透林岑身体的那些铁枪的样子,他才十七岁,脸上就沾满了血腥风尘。
毕安推门进来,将宫人手中的汤药递给我。
我瞧着这汤药同我这几日喝的有些不同,但还是没犹豫,一饮而尽了。
“这是避子汤,小卓子你可记好了,万不可出差错。”毕安说道。
“哎——奴才记好喽,万万不会让殿下的子嗣有差错。”小卓子从毕安身后钻出来,拿着个册子写着什么。
我见毕安身后的宫人都互看了看脸色,又都心照不宣地沉默额垂下头来。
我想这是毕安的主意,坐实了我和陈棠月有肌肤之亲,让那些宫人皆恭敬待我。
“殿下正忙着呢,随我去殿中侍候纸墨吧。”毕安扬了扬拂尘,带着我出了殿。
才踏进殿门,就见杜静安在殿中跪着,陈棠月在桌案上披着什么文书,殿中气氛有些僵冷。我默声走上殿上玉阶,将毕安给的笔墨呈到案上去。
我能感觉到阶下那一双眼正看着我,磨好墨,我便垂着头立在雕花屏风前,我并不知这杜静安哪处忤逆了陈世子的心意。
“月末吴修便要启程回吴,你以后跟着他吧。”陈棠月刚批完了一叠,小卓子便又抱来厚厚一叠文书。
“殿下,这是各州县地方官上表文书。”说罢,小卓子便到阶下候着了。
“殿下这是要弃我?”杜静安抬头看他,双眸泛红,却将眼睛睁大强撑着,说话的声音有些颤。
陈棠月听了,却没什么反应,只拿了文书来继续看。
殿中的氛围更加僵冷,一时之间无人敢言语。
陈棠月拿着笔在砚台端沿敲了两下,清脆地玉石敲击声让我回过神来,我抬头去看,发现砚台的墨已经干了,只余那条墨龙还在张牙舞爪着,我忙上去研墨。
“静安已跟随殿下良久,也为殿下做了不少事,”须臾,杜静安才颤抖着开口,“静安求殿下念在往日的主仆情份上,让静安去侍候总督大人吧。”
陈棠月听了却还是没有反应,硬生生地将杜静安晾在一边。
杜静安咬了咬唇,低下了头,掩了委屈。
我闻言倒是惊了一惊。王雁路是五品京官,王瑶在赴宫宴时往往受尽欺辱,唯有杜静安与之交好,后杜家又提拔张久川,原来是为门当户对做打算。只是京都皆知张久川爱慕王瑶,上门提亲达三次之多,次次被婉拒门外。想来是王瑶为成全杜静安的心意。杜静安帮扶王瑶,或也是为了让张久川知晓她的好意。
只是苦了阿泽和林家军,为了这么一个儿女情长的事,失去了许多提升机会,被迫驻扎京郊练军营。
临近午时,毕安进来请陈棠月移殿用膳。这时陈棠月才将笔搁置一边,起身走下殿,到杜静安身边时,缓缓道:“你做事的时候,可念过主仆情分?”
杜静安身子一颤,待陈棠月出殿时,她竟身子一软,跌坐到地上。
我从未见过她这般颓唐狼狈的模样,像是失去了所有斗志,全然不见往日高傲的样子。
“越西,你真是好手段。”杜静安突然这么对我说。
我没有答她,也不知该如何答她。
她看着我,双眸满是不甘和愤怨,她张了张嘴,似乎还想说什么。
“越西,愣着做什么?要殿下候着你不成?”小卓子唤道。
我闻声忙错开杜静安的目光,跟着小卓子出了殿。
我在偏殿呆了半月,跟着毕安去偏殿是往往只需在一旁候着,用膳梳洗皆由毕安领着宫人侍候,我不过研墨添灯罢了。
三月初,毕安说陈棠月要回陈宫了。半月来,呈上的文书越来越少,上回见他在处理州县地方官的文书,我就知道他快将越国洗干净了。
几日之后,陈国世子下令全国废弃旧朝分封制度,立燕云娄岐南之子娄良宵为承奉侯,入住旧越宫,由大将军林甫摄政,原越王室中被放逐者皆需换姓更名。自此,越国为陈国附属,无主无臣。
毕安念诏书时,我就站在殿前玉阶上,阶下立着新朝的文武百官,娄良宵一人站在前面,俯身跪地接旨。林甫、林泽、娄岐南皆立在后面,跟着娄良宵俯身跪地。
入住旧越宫?越宫已被焚烧成灰烬,那里还能入住新主?想来是陈世子给的难堪。
林甫受令毒杀娄岐南的原妻,娄家原本便于林家势如水火,如今看来,陈棠月是要两家相互牵制了。
阿泽垂着头,我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他冷了许多,从前眼中的明媚已全然不见了。
想来我也不比他好多少,我已经许久不曾看过铜镜里自己的模样,我害怕看见自己无力又麻木的样子,似乎和行尸走肉无甚区别。
“臣接旨。”阶下略稚嫩的声音传来,我抬眼看,娄良宵着了墨蓝的衣裳,胸口金线绣的朱雀没有像那日娄岐南下袍的朱雀那样嵌着血红的玉石,看起来十分无神。承奉侯?承谁的恩?奉谁的命?
我在心里默叹了口气。严冬过了,波澜初静,也总算尘埃落定了。今年的春天要比往年好过些吧。
本书由潇湘书院首发,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