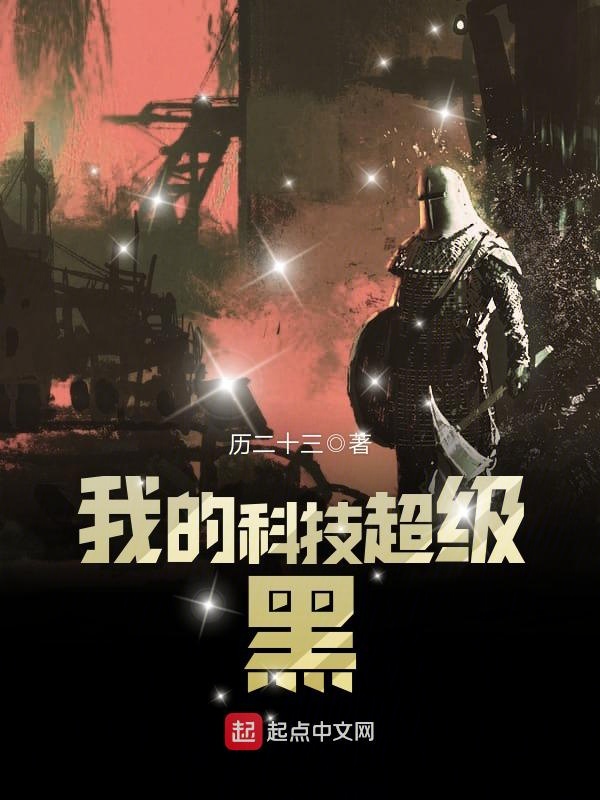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季夏之歌》第十九章 免费试读
姜缱即刻收拾行李和马车,若姐姐真如季予所说在越邑,那此处她一刻也不想待了。
姐姐的事情她不便与人说,可是偏偏季予那一双眼睛生得深邃仿佛会说话,指责起人来竟饱含怨怼,火力十足。
冷漠?**?毫无诚意?姜缱用力按住胸口,她觉得心里好像揪起来一块,久久不能抚平。
从纶邑至越邑,不过七八日。姜缱思念姐姐,行路飞快,六日便已到达邑中。这一路她想了许久,姐姐若真成了王子余的内嬖,宫墙壁垒,不知要如何相见。
听闻越邑乃夏后少康专为供奉大禹之墓而建,又将王子余封到此处做越伯,监督祭礼,可见禹皇之神台便是越邑中最重要的所在了。
夏人重祭祀,如逢*节,越伯宫人必前去庙宫祭祀,姜缱想,如自己在庙宫守着,倒是可以碰碰运气。
只是这法子,慢了些。自己离开巫寨已二月有余,不知萝儿可好,不知阿媪照顾萝儿可觉得吃力。她有些牵挂她们。
姜缱在禹皇神台近处寻到一处逆*,随意住下,仍以贩药为生。她每日将药草背到庙宫高台下,将来往行人都看在眼里。
牵牛星与婺女星,相隔于银河两端,日渐靠近,七夕之日,转眼到来。
越邑百姓走到街市中,身着彩衣,载歌载舞。越地多河泽,越人的歌,婉转而多情,如同水一般柔美。
在漫天欢笑和舞乐之中,姜缱瞧见远远驶来一辆骖驾,御人着官服,手持铜镶皮鞭。待那车辇近前,御人将帘子抬起,车中走下一个青*男子,锦衣高冠,轮廓与季予有些相似之处。
越人忽的将那马车团团围住,纷纷喊道:“邑君!邑君!”
他便是仲余了。只见他忽然回身,向车上伸出手。姜缱立刻站起身去看。
一个纤纤女子从车中探出身来。她皮肤白皙,乌发如云,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她头发上簪着一根流光溢彩的翡翠发簪,从远处便一下子能看见那夺目的绿色宝光。
姜缱认得那簪子,从前在濮国时姐姐每日都会戴着。
“姐姐……”*幸,你还活着。不知何时,姜缱脸颊湿了。
庙宫前本就拥挤,越伯和姜缗的到来,吸引了更多的百姓。仲余缓缓挥着手,和围着的人们说着什么,人们并不散去,而是给他们让了一条道儿,通向庙宫。
来夏之后,姜缱曾多方打听王庭女子的详细。她知道越伯还是王子余时,便已娶了姬氏宗姬为王子妇,从未听闻有濮**王子妇,想来姐姐应该是庶妇吧。姜缱心中*分感概,既高兴,又心酸。
“邑君!邑君!”姜缱挤上前,手中举着几棵干草,大声道:“买些瑶草吧!妇人用了不仅皮肤白润,还香气袭人呢。”
那声音如瑶草一般玲珑,穿透闹哄哄的街市,让姜缗浑身一颤。
她回过头来。看到姜缱,立刻双眼圆睁。她推开人群,走到姜缱身边,呆呆将她看着。
“缱儿……”她向姜缱伸出手,“是你吗?我又发梦了么?”
姜缱看着她,傻傻的笑着,“姐姐……”
姜缱被接入了越宫。七月初七,日月逢七,星辰初聚。果真是好日子,姜缗想。
热水伴着瑶草的香气,氤氲在暖室。姜缗将姜缱的头发散开,用米汁轻轻搓洗。
“傻缱儿,瞧你把自己折腾的,奇装异服就罢了,头发也乱糟糟的,姐姐帮你好好梳洗。”
姜缱整个人泡在水中。她回过头看着姜缗。自从重逢,她便止不住笑意。
姜缗比从前瘦了些,神情气度与从前无异,不似窘迫忧愁。姜缱放下一半儿的心。
“姐姐,你还活着,太好了。”
姜缗眼圈发红,“缱儿,那时濮国战败,我亦以为你随父亲、母亲、长兄一起殉国了。”
“我逃走了。”姜缱眼中似有*千回忆,却只轻叹了一声,“濮国无处容身,我便去了巫咸。”
相比于自己,姜缱知道姐姐能活下来更加不易。她自嘲,她们两姊妹究竟做错了什么,一个差点被逼殉国,另一个差点被人殉葬。
姐姐曾是弋王寒戏的王妇。
彼时弋邑被攻破,寒戏战死,寒戏的父亲寒王则被生擒送至纶邑。
天下人皆知,大宰伯靡亲自督刑,将寒王凌迟处死,曾经轰轰烈烈、名震天下的寒氏一族全族灭顶,只剩下夏后氏为了平息世人议论而造的衣冠冢。
姜缱曾以为姐姐作为王妇,要么随弋王陪葬了,要么于战乱中受辱而死。若不是高阳承提醒,她不会觉得有其他可能。
能找到姐姐,还是要感谢一个人。王子予……姜缱这几日总是想起他。
他那样指责自己,她应该很生气,可是末了,她却只觉得心里酸酸的。她就是块木头也能看出他的好。他那么热情,那么直接,就像是炎夏的日光,炽烈极了。面对他,她只想逃走。
姜缗缓缓说道:“那时,弋邑被攻破,弋王被擒;弋邑男子皆战死,老弱妇孺充为奴隶。我本在人牲之列,是邑君救了我。”
人牲。姜缱死死握住自己的手。
她问道,“越伯……可知晓你是濮人?”
“自然知晓。父亲与寒王联姻,夏人怎会不知?甫一开始他便知晓我这弋王妇是濮人。”
姜缱忍住眼泪,“那如今姐姐便是奚奴了?我真是罪人,这些*让姐姐在此受苦。”
姜缗摇头道:“邑君……待我很好。他将我藏在越邑,让我免去了给弋王陪葬的命运。”
“那他的小君呢?她可曾为难你?”
“怎会呢……她出身高贵,而我不过区区庶妇,又是奴籍,无论如何也不会威胁到她的。”
昨日在街市,看仲余的举止间对姐姐颇为在意,倒不像是将姐姐当作奚奴。
不过谁都明白,身为罪奴,是**任何自由和自主可言的。如今有越伯怜惜,日子尚可过下去,可将来若有一天他对姐姐不再有情义,生杀予夺不过是他或者小君的一句话。
“姐姐,你……可喜欢越伯?我瞧着,他对姐姐似乎不一般。”
“傻缱儿,也只有你会这么问我。”姜缗淡淡说道:“我是罪妇,能活着已经是他的施舍。此生,我已心死,不过是过一日算一日罢了。”
活在别人的施舍下,这是怎样的日子?姜缱不敢想。
姜缗拿出一块细白纱布,替姜缱仔细擦拭发梢的水滴。
“姐姐,我去求邑君放你奴籍可好?你可愿随我去巫咸?”
姜缗手上一顿。
“金银铜贝我都有许多,你若离开越邑,绝不会为以后的生计发愁。”
“不必白费力气,他不肯的。就算他肯,如今濮国已灭,又有何处是你我的家园?”
“姐姐,巫咸山水秀美,可以避世。你……不愿同我在一起么?”
姜缗沉默良久,缓缓道:“避世?邑君同我说,近日大宰伯靡欲伐巫咸,如今巫咸已非一方净土了。”
心中有什么直直下坠。姜缱急问:“可知因何而伐?”
“不知,他不曾提及。”
长发结成辫子再绾成髻,穿上姐姐准备的织锦华服,姜缱打量铜镜中的自己,已是濮国淑女的模样。她面色平静,可实际心乱如麻。她离开巫咸之前,那里风平浪静,如今却起了战事。她有种预感,此事一定与高阳承有关。他之前说过的那些的话,如巨石压得她喘不上气来。
她将高阳承要报**复国的话告诉了姜缗,姜缗一下子紧紧抓住她的衣袖。
“缱儿,无论他做什么,你不可再与他有任何瓜葛。”
姜缱却暗自下了决心。“姐姐,我若不管承,他会死的。”
姜缗脸色煞白,“你要做什么?你我重逢如此不易,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有任何事,否则我死了也无颜面见父亲母亲!”
她哀哀劝道:“缱儿,邑君对我多有照拂,不如你在越邑住下,陪我一些时日可好?”
姜缱沉吟片刻,打定了主意。
她握住姜缗的手,笑着安慰道:“姐姐宽心,我并非要去涉险,而是要去请愿,将濮地的事情禀于夏后罢了。待这事儿了了,我便回来见姐姐。到那时,若姐姐愿意走,我和你去巫咸。”
“不可!姒少康若知晓你出自姜氏,说不定会杀了你。”
“姐姐多虑了。”姜缱安慰道:“姜元一族如今在濮地不是好好的?封邑较之从前还多了些许。濮地多是姜氏和高阳氏的后裔,根深叶茂,杀得完么?更何况,我这是利国利民之事,天下人都看着,姒少康断不会如此愚蠢。”
一席话令姜缗惊疑不定。姜元是父亲的长兄,也是他们姊妹俩的伯父。
当*濮国战败后,姜元便第一个出首,告发父亲与寒氏的来往细节。
夏后氏抹平了濮国王族嫡亲一脉,近身的寺人和小臣都未放过,却重赏了姜元。如今他这一脉在濮地甚是风光。
姜缗愤懑的握紧了拳头。她知晓此去不可能如姜缱说得这般平和,可是妹妹自小就十分倔强,她既如此说,便断无被劝服的可能。
姜缗引着姜缱,拜见了越伯和越伯之妇小君妇安。
妇安名唤姬芸,安伯之女。姬氏,传承自轩辕黄帝,祖上封有安邑,延续至姒少康一代,如今已是濮地的新主,夏后新封的濮伯姬显,正是姬芸的叔父,安伯姬轲的弟弟。
今**是寻常拜见家主。仲余穿着米白深衣,做家常装束,想来是不愿令姜缱拘谨。姬芸却满坠珠翠头饰,玄衣金舃,虽衣着华贵,可与仲余坐在一起,一黑一白,看着怪异极了。
向越伯和小君行礼之后,姜缱颔首肃立。拜见夏后不过就是如此装束了吧,姬芸却这样隆重来见一个家奴,姜缱摸不透姬芸心思,面上越发恭敬。
昨日初见时,因姊妹二人重逢,激动落泪,仲余只礼貌性的问候了姜缱,便不再打扰她们二人,表现得颇有修养,加上他于姐姐有恩情,姜缱对他印象不坏。
今日见到仲余的小君,却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姐姐虽说姬芸不曾为难她,但姜缱从小长在王庭,妇人之间的争斗见得多了,自然明白是怎么回事。
姐姐性子柔顺,如今只想在越地讨一份生活,可主母若把她视作劲敌,她未来就艰险了。更何况,如今濮邑新主正是姬芸的叔父,无论怎么看,姜缱都忧心不已。她暗下决心,待濮人的事情完结,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姐姐,随自己离开。
姜缗和姜缱两姊妹并肩立在下首,容貌和身形皆肖似,仿若并蒂之花。仲余瞧着,一个柔弱如春之樱,一个娇俏如雪中梅,他只觉得屋中莹白的秋兰都失色了不少。
“妇姜,”仲余笑道:“往日听你提及汝妹,如今见了,果真不同凡响。”
说罢细细询问姜缱巫寨的光景,族人,生计,是否婚配等等。姜缱为避免麻烦,搬出从前在巫寨的说辞,道自己居于阿媪的寨子中,育有一女,夫君于战乱中丧生。
姜缱平静地说完,姜缗的眼眶却红了。姜缱冲她笑了笑,她们姐妹二人,竟总是在替对方难过。
仲余道:“妇姜之妹,亦是仲余之妹。今日设宴,便是庆贺你们姊妹重逢。今后,濮姜便安心在越邑住下,我遣人将阿媪和萝儿接来同住,可好?”
姬芸转过头,看了看仲余。她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因为妇姜的事生气,仲余却浑然不知。
她双手攥紧捏住衣袖,面上挤出一丝笑意,“正是如此。濮姜姿容出众,可惜造化弄人,大好*华竟丧夫寡居。”她看向仲余,“邑君不如寻一寻越地的氏族俊杰,给濮姜觅一门良配。如此,不单伊人可在越地安心住下,连妇姜也去了一块心病了。”
仲余略有些意外,“哦?吾妇热心,可……越邑如此偏僻,恐不易寻到合适的才俊。”
姜缗亦转过头看了看姜缱。姜缱表面虽不显什么,却是十足骄傲的人,姜缗知道她绝不会接受仲余的安排。
姜缗正要想个理由拒了,只见姜缱果然跪倒在地,郑重道:“多谢邑君和小君美意,缱十分感激。邑君于水火之中保全了姐姐的性命,便等同于救了缱。一直以来,缱以为姐姐已不在人世。曾日日锥心,夜夜噩梦。邑君于我姊妹,实有再造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日邑君若有差遣,缱必*死不辞。”
姜缗将姜缱扶起,看了一眼仲余,缓缓道:“邑君和小君仁善,何须你一个女子去做那些凶险之事?缱儿于我,也是同样。如今见你安好,姐姐此生再无他求。”
姜缱笑了笑,又道,“至于亲事,缱实在无心力考虑。今日缱其实是来辞行的。”
仲余吃了一惊,“为何?寺人可有何处不妥?又或是有何不习惯?”
“并无不妥,谢邑君照拂。”姜缱道:“只是如今有一件紧急的事,缱须面谒夏后。”
仲余又吃了一惊。他心中转了几个圈,见姜缱不是在开玩笑,神色凝重起来。
“濮姜莫不是在玩笑?夏后不是寻常百姓可以见到的。”
“并非玩笑。邑君知道,我姊妹二人是濮人。”姜缗悲戚道,“如今濮地天灾,濮人艰难,我等不可坐视不理。”
于是将姬氏和雍氏在濮地课重税敛财、肆意奴役百姓等事一一道来。仲余皱紧了眉头,而姬芸更是心惊肉跳。濮伯姬显是她的叔父,他若果真如此行径,夏后知晓必不会轻饶。
“今*濮地天灾,民生更加艰难,濮人纷纷逃离家乡,乃不得已也。”姜缱道,“若濮伯不收敛,流民只会越来越多,到时只怕不止与濮地相邻的巫咸,大夏各处都会流民遍野。”
“邑君……”姬芸急切道,“叔父向来小心谨慎,绝不致如此昏庸。想来此事恐有内情,应由叔父亲自面见夏后,以免生出误会。不如,由我修书一封,送去濮邑吧……”
由谁去说,姜缱是不在意的。只要姬显以后不再如此苛待濮地百姓,不征收重税,濮人可安稳度日,便不会去做那流民,流民少了,高阳承便起不了其他心思。她想要的,不过如此。
她盈盈下拜,“小君思虑周全。缱并无异议。”
姬芸面色稍缓。
仲余将芜杂的思绪捋了捋,却觉得不妥。
流民与日俱增,大宰已去巫咸平乱,尚未有消息传回;濮地那里,是长兄孟衡去的,可是自己对衡的事,更是知之甚少,不知其中有何曲折。如果以孟衡小王之尊,竟为姬氏遮掩,此事必牵扯巨大。
他瞧着眼前的姜缱,见她神情不似作伪,心想,不如就由她去出面捅破,无论结果如何,于自己都**坏处。
仲余斟酌道:“濮姜曾是濮人旧主,由濮姜为民请愿,倒颇为合适,夏后定然格外重视,于濮人有益。”
“邑君!”姜缗和姬芸同时唤道,仲余摆了摆手。
“吾妇不必忧心,夏后圣明,必不会让濮伯蒙受不白之冤。濮姜心系濮人,深明大义,我等作为臣子,理应同濮姜这般,为夏后分忧,为社稷着想。我等应备上文书,差遣从人,助她谐阙。”
“邑君,我……想陪缱儿一起去。”姜缗说道。
“不可!”姜缱和仲余同时说道。
仲余说:“缗儿,你莫要忘了,‘弋王妇’至今下落不明。若是被人知晓你的身份,拿你去填了殉葬坑也未可知,届时便是我和小君,也要担下罪责。”
姬芸的脸色彻底阴冷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