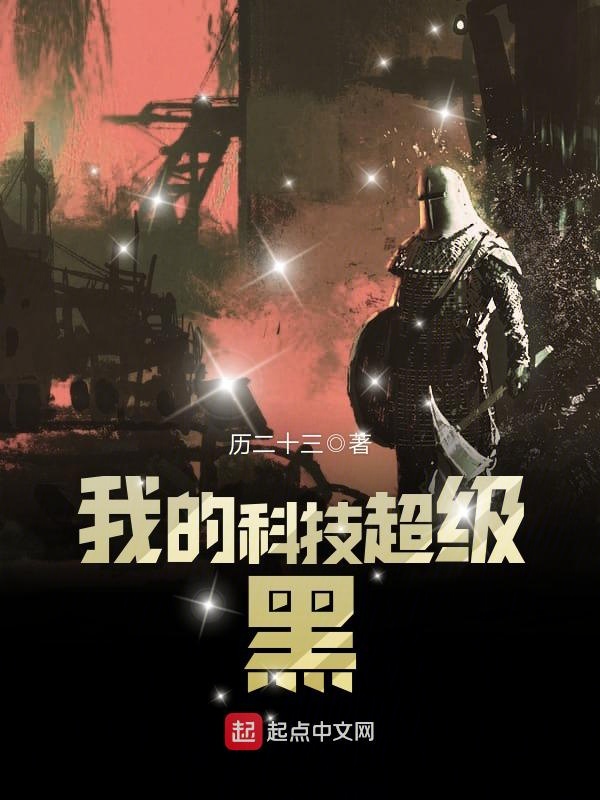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紫冰夫人》第11章 奇案 免费试读
煜华公子感觉到了什么,忙问道:“你这么问,可是知道些什么?”
黑甜犹豫了片刻,说:“不知煜辉公子的性情如何?”
“性情么?”煜华公子沉吟道,“辉儿聪慧,喜读诗书,又擅骑射,平日待人也极为亲善——只是,他的母亲秦小娘出身低微,在府里谨小慎微惯了,对他的管教也忒严了些,慢慢变得有些胆小怕事起来。”
“你说他胆子小?”黑甜激动起来,“他最怕什么?”
“他啊,蛇虫鼠蚁、鬼怪精灵,没有不怕的!我时常笑话他,说他就像闺中少女一般。”
“我猜,他一定最怕虫子,而且,是毛绒绒,颜色艳丽的那种!”
“对了!”煜华一拍额头,说:“辉儿来此之前,正好被一种虫子蛰过,痛得在床上直哭,几天下不了地。从此怕极了那种虫子,就是你刚才所说的,肉乎乎,浑身长刺,有黄绿相间的颜色,十分艳丽。”
又奇怪地问她:“你怎么知道得如此清楚?”
黑甜点头微笑道:“谜题可以解开了。煜辉公子的死因,极有可能如此。”
煜华更加急切起来:“快说,到底是因为什么?”
黑甜安慰他道:“公子别急,且听我来慢慢跟你解释。”
借着月光,她指着桥头的那棵百年江枫说:“公子从王家出发去灵泉山,必然经过这座桥,还有桥头的那棵大树。那棵树不是寻常的树,而是一棵百年江枫。”
煜华看过去,那棵江枫隐约可见。“那又如何?”他问道。
“枫树最易吸引一种叫树喇子的毛虫,寄居在树上,靠食用枫叶为生。每年七月到九月最为密集。”
“莫非蜇过辉儿的那种虫子,就是树喇子?”煜华似有所悟。
“正是。树喇子不时落掉下来,有的却不会直接**,而是像蚕儿一样,扯着根细丝,一头悬挂在树上,身子吊在半空中,于是有人戏称它为‘吊死鬼’。”
“如果树下刚好有人路过,就会和树喇子碰个正着。那日煜辉公子骑着马从树下经过,极有可能恰巧中了树喇子的埋伏……说它是‘恰巧’,实是因为有时会碰上,而有时碰不上,至于何时碰上,何时碰不上,何人碰上,何人碰不上,全在‘恰巧’这两个字上了。”
“煜辉公子本来就怕极了树喇子,现下又发现自己头上身上落满了树喇子,自然会惊慌失措,行为失常,就像旁人看到的那样,像突然发了疯一般。”
“所以,马才受了惊……”煜华若有所思,沉默片刻又疑惑道:“可是,我们也询问过不少当地村民,并无一人提及虫子伤人的事情。”
“公子有所不知,村里人管这种虫子叫野蚕儿,不但不怕它,还把它当作一种美味。”
“常有些人抓了这些虫子带回家,用枫叶来养着,等过几天长大长肥了,就用来炒着吃,或者油炸。我也尝过几回,表皮酥脆,内里香软,极可口的!”
“乡下人见惯了各种虫子,就算被蜇着了,也不会惊慌失措。”
“而且,被蜇着以后,感觉因人而异。我就被蜇过几回,也不觉得有多痛。我表姐细雪却痛得直哭,一连好几日茶饭不思,且难受呢,从此以后,她每次过桥,都要绕着这棵江枫走。不过,像她这样的也是少见。”
黑甜又说:“今儿中午我就在枫树下躲日头,看到地上斑斑点点的,尽是死去的野蚕儿掉落下来,又被村民踩踏后留下的痕迹。”
“公子若是不信,等天亮了以后,再来查看一番就明白了。”
“可是,辉儿打捞上来以后,身上明明没有虫子——是了,定是辉儿落水后,虫子已经悉数被河水冲走!”煜华长叹一声。
“仵作验身的时候,倒是看见辉儿脸上、手上有些小小的红色疙瘩,以为是蚊虫叮咬所至,没未在意……”
“明日我定会来此查看,还要请负责此案的官差来验过。如果确是野蚕儿伤人所致,我定会速回江城禀明主君和秦小娘,辉儿也从此得以安息。”
煜华公子说完,朝黑甜深鞠一躬,说:“多谢姑娘点拔!姑娘聪慧,足令男儿汗颜!”
又问黑甜:“可否请教姑娘芳名,日后定当重谢。”
他见黑甜犹豫不决,又解下腰间所佩一件物什,说:“这是我的心爱之物,名叫翳珀。送于姑娘,聊表谢意。”
“这……”黑甜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得知是公子的心爱之物,原是想接的,可接了又怕让公子觉得自己有所企图,竟是为了邀功领赏来的,一时手足无措。
就在这时,忽听得有人在“公子”、“公子”地叫唤,紧接着,又有脚步声和喘气声由远及近地传过来。
煜华公子一把将那翳珀硬塞到黑甜手里,说:“是我的随从来了!姑娘快走吧,让他们看到,只怕有损姑娘清誉。就此别过,我和姑娘改日再叙!”
黑甜来不及多想,只得接了翳珀,趁着人影还在一箭开外晃动,朝着村里的方向跑进阴影里。她身轻敏捷,很快消失了踪迹。
天色大亮后,煜华果然骑着马从王家出来,像煜辉坠马那日一样,打马直奔马嘶桥。
就在经过桥头那棵百年江枫时,突然感觉脸上一凉,忙用手一摸,手心顿时火辣辣地灼痛起来,定睛一看,竟是几条黄绿相间密密长满毛刺的大肉虫——虽说他平素称得上胆大气盛,无所畏惧,还是不免被吓得惊叫一声,用力甩起手来。
好在他很快甩掉了虫子,掌控了局面。下马略平复心绪后,他发现自己还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再一看手心,那里果然起出几粒小小的红疙瘩,虽然不甚起眼,但痒痛无比,让人忍不住想去抓挠,然而越抓挠,越痒痛,惭惭地,红疙瘩变成了水泡,水泡又开始溃烂。
“看来那姑娘说得没错,辉儿定是被这虫子惊扰,意外坠马。可叹辉儿空有满腹诗书,一腔抱负,竟在舞象之年折在了几只小小虫子上了……”煜华不禁伤感自语道。
出于谨慎起见,煜华即刻请来负责此案的钱推官,再次勘验现场。钱推官听煜华说起野蚕儿的事,这才陡然想起三十年前的一桩奇案来。
“三十年前?”煜华不解道。站在他面前的钱推官明明刚过而立之年。
“那是我的业师经手过的案子,”钱推官忙解释道,“说它‘奇’一点不为过,因为闻所未闻,估计此后也不会再发生。这让他一直念念不忘,许多年过去了仍将它挂在嘴边,当成件新鲜事儿时时谈起。”
“那是在仁宗至和二年,江城有个姓周的老乡绅,平素最喜‘小舒服’。”钱推官做了个掏耳朵的动作。
“周老太爷的儿子是个大孝子,为了讨父亲欢心,千挑万选地找来个技艺超群的挖耳师傅,好酒好饭养在院外租来的小屋里,就为了隔两天便伺候老太爷一次。”
“有人见识过那个挖耳师傅的手艺,说他‘一勺一刷一铲收放自如,一推一捏一掸轻缓有道’,足让人身心舒坦、耳聪目慧,尘世凡事,恍若空灵。”
“难得这个挖耳师傅与周老太爷极为投契,周老太爷对他也极为信任。不知不觉五六年过去了。”
“有天挖耳师傅偶然谈起心事,说离家久了,甚是记挂家中妻儿。周老太爷便亲自出面,在后院挑了间下人住的宽敞些的厢房,说是要让他安置家眷。”
“挖耳师傅果然把家眷从乡下接了来,住进厢房,一家人对周老太爷是千恩万谢,感激不尽。”
“不久后的一天,屋里闷热,周老太爷想在院子里享受‘小舒服’,就让下人搬了躺椅放在树荫下——悲剧就在那时发生了。”
“挖耳师傅突然发了疯,手里拿着银鎏金的挖耳勺,对着周老太爷的耳朵就是一阵乱捣乱捅……只见鲜血飞溅,周老太爷连声惨叫,当时就晕死了过去。”
“周老太爷年老体弱,经不起这样的伤害和惊吓,没过几日就撒手归西了。周家人恨透了挖耳师傅,很快报了官,一口咬定他恩将仇报,故意杀人。那挖耳师傅连呼‘冤枉’,无论怎样严刑拷打都拒不认罪。”
“业师当时任江城提刑,深觉此案蹊跷。犯人并无作案动机,却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止癫狂,极有可能是心疾或癔症发作。然而郎中仔细查过,犯人精神并无异样。”
“业师询问口供,犯人坚称自己冤枉,之所以举止癫狂,失手伤人,是因为手背上突然出现了几只毒虫。还煞有介事地描述那虫子的特征:肉乎乎,浑身长刺,黄绿相间的颜色,十分艳丽狰狞。”
“犯人声称,小时候曾被玩伴捉弄,将数只毒虫从领口塞进贴身衣衫,被蛰得浑身红疙瘩,痛极痒极如同钻心,调养了月余才略为好转,所以深惧了那毒虫。”
“没料到在挖耳的紧要关头,那毒虫竟突然出现在手背上,他自然惊惶失措,方寸大乱。纯属意外事故,绝非有意为之。”
“业师亲去勘验现场,却没有发现犯人所说的毒虫。因为证据确凿,犯人虽不认罪,仍以故意杀人罪定刑,被秋后问斩了。犯人在临刑前仍然大呼‘冤枉’,这让业师耿耿于怀。”
“案发后的第二年九、十月间,业师再访周家案发地,果然发现有家禽在地上啄食些什么,仔细一看,竟是些黄绿相间的肉虫子。”
“抬头看去,只见头顶上方树叶茂密,上面爬着的,就是那种黄绿相间,艳丽狰狞的带刺毒虫!”
“业师方才明白过来,那挖耳师傅说的是实话,他果然是被冤枉的。虽说已经造成伤人之实,但罪不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