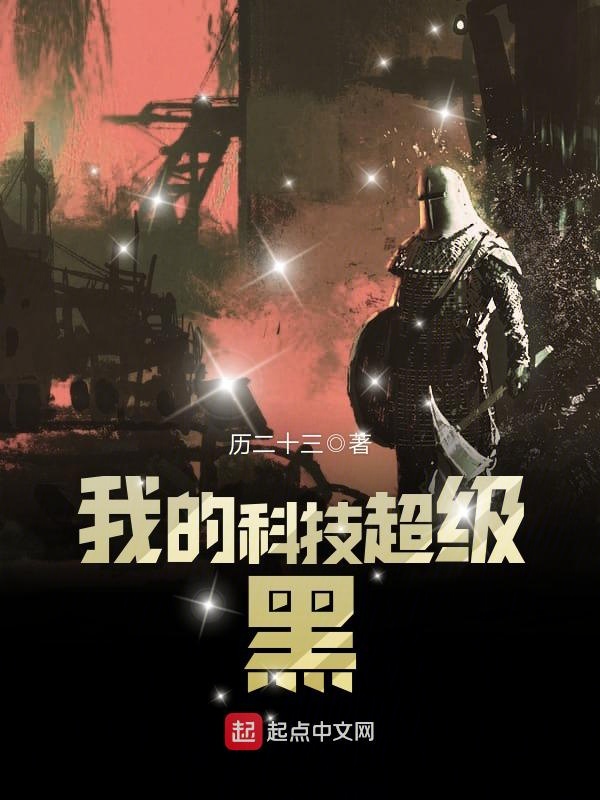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我和十三皇子》第十章 赛马 免费试读
梁九功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捧着那尊海螺仙子像走人,一刻也不想跟阿妈多呆,断炎翡没丢那阵我都怕她怕的要命,现今断炎翡丢了,我心虚的不得了,甚至不敢直视她的眼睛。
皇上要摆驾谦府的事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快地传遍了整个京城。一时间,谦府仿佛成了京城中炙手可热的香馍馍,大小官员、商贾贵人络绎不绝地前来拜访,都快把谦府的门槛踏破了。
我盘腿坐在贵妃椅上,啃着手指甲一筹莫展,外面门庭若市,我却愁云惨雾,再过几日皇上就要来了,会不会再次问起断炎翡呢?这我可不能赌啊,到底该怎么办?要不扯那嫁衣上的一颗珠子去当铺淘一块差不多的应付应付得了……
就在我无计可施、胡思乱想的时候,萨梅跌跌撞撞冲了进来,她绊倒在小方桌上,直接跌在我面前,把铺在方桌上的桌布拖得滑到地上。
“你再这么毛毛躁躁的,信不信我把你卖了,就卖给京城的人,让你永远也回不了拉萨。”我气死了。
她脸蛋涨的通红,急道:“不得了,东窗事发了!”
我猛地站起来:“阿妈知道我打人了?”
萨梅摇摇头,指着外面,“你的断炎翡……来这儿了。”
我和萨梅一前一后趴在花厅外面。花厅里焚香煮茶,阿妈正在招待一个双眼凌厉胡须卷曲的伯伯,坐在伯伯身边的正是前几日在街上被我一脚踹入河里的钱晋锡,他大喇喇地穿着紫色的丝绸袍子,领口开得很大,露出了雪白的脖颈,脖颈上挂着的正是我的断炎翡!
一定是我酣畅淋漓一脚把他蹬入水里的时候掉了,说实话,看见断炎翡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毕竟是找到了!
“老夫本想等白里回京之后再来恭贺,可总不能人人都来了,就我们钱家还没来啊,以咱们两家的关系,我们没有跑在前头就是不应该的了。”伯伯中气十足看样子应该是那个吊儿郎当的坏小子的父亲!
“咱们两家是故交,况且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还要劳烦大人亲自跑一趟,实在是过意不去。”额娘如此道。
“当年我儿同世侄女一同拜在儒学大师海康先生门下,是同门师兄妹,如今世侄女回京数月,小儿理应来见见师妹。”
阿妈微微笑道:“七月刚满两周岁便被送回拉萨,虽拜了海康先生为师,却从未在门下受教,也是白担了这个名。”
“虽然如此,但海康先生一生单薄,对外承认的就是我儿和世侄女两个徒弟,这个名是担定了。”
钱晋锡插嘴道:“伯母,小师妹的大名传遍京城上下,可我都还没见过呢!这次你怎么也得让我见见小师妹吧。”
他说‘小师妹’三个字的时候嘴角扬起了玩世不恭的笑容,若不是我做贼心虚趴在花厅外面,准得恶心的把早饭给吐出来。他是京城贵族,又是乌雅家的世交之子,还与十三阿哥他们是好友,又有个听起来很了不起的师父,怎么就长成这样了?比那个卫徉还要油头粉面。
阿妈不可能没看见那么明显的断炎翡,但她不动声色,像是什么都没发生一般笑容可掬道:“月儿病了,怕是水土不服,许久都不见客。怕是要让世侄失望而归了。”
我全身上下一阵哆嗦,不知是因为阿妈撒谎的技能炉火纯青,还是那声温婉若水的‘月儿’。
钱晋锡和他父亲走后,我找杜自芳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钱晋锡的父亲是大理卿钱兴安。萨梅看着他们离去的马车急的乱蹦,非要让我去追,我想了想,要知道我可是一脚把他踹河里去了,如果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去问他要肯定不行,既然他毫不顾忌地戴在身上,说明他不知道那是断炎翡。万一打草惊蛇后他怀恨在心,不仅不还,还反咬一口,那可怎么办?
我战战兢兢地喝了一口松露菌子汤,斜眼瞟了一眼阿妈,她吃了一点去刺后的鱼肉,面无表情地抿了一口茶。
‘难道是没看见?’我在心里琢磨,‘不可能啊,那么明显。’
我故作淡定地吞下含在嘴里的汤,告诉自己要稳住,千万不要不打自招。
“好吃吗?”
阿妈突如其来说话差点让我呛到,我忙点点头,不敢咳出声来,生怕这样会显得太可疑。
“你知道断炎翡是什么吗?”她说道,“我想把上次的话说完。”
我张口结舌,一时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再不说,你会把断炎翡当做儿戏,想送谁就送谁。”
我知道理亏错,但仍小声辩解:“我怎么可能把断炎翡送给姓钱的呢……”
“那为什么会在他那儿?为什么别人身上的贴身之物不会丢了,只有你的会丢?”
我把筷子捏得吱吱作响,手都发白了,才发现它们是纯银的,撇不断,就索性放下来:“断炎翡丢了是个意外,你不要说的那么难听。”
“意外?我早就跟你说过要谨慎行事,可你好大本事,竟然把它随便丢了。”
“不是随便丢的,”事到如今我突然特别想解释,可火气外冒,解释的话也条理不明:“他调戏姑娘,我教训教训他,就把玉丢了,没曾想竟然被他捡了去。”
阿妈脸色铁青:“你以为你是谁,有什么本事去教训大理院的少爷?”
“大理院又怎么样?”我总算发现了,只要跟阿妈讲话,都会不自觉地会偏离原来的主题,直奔大吵特吵的局面而去:“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看不过去就要管。”
“不知轻重。”
“我不知的是你们京城人眼中的轻重,我只分得清是非,一块玉而已,丢了就丢了,我不稀罕,也不在乎。”
额娘再次扬起手来要打我。
杜自芳和花朵嬷嬷跑过来劝。
我看着她扬起来的手,仿佛已经想起了被抽耳光的火辣辣,气的不知所以,猛地站起身来,碰翻了菌子汤,汤汁溅到了旁边的盘子里,染白了红通通的糖醋里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既然这么讨厌我,就不该去接我回来!”
我一脚踢开面前的凳子朝府门口奔去,那一刻什么都不想要了,只想着就此消失,让这些人后悔去吧!却一头撞入来人的怀里,我后退两步,揽了揽撞乱的发丝,刚想骂人,就听见追着我来的杜自芳讶异道:“老爷回来了?”
老爷是谁?户部尚书乌雅白里,我阿爸!
我盯着眼前这人,他慈眉善目,容貌清雅,双眼明亮,却很温柔,一身青衫风尘仆仆。
他背着手,笑眯眯地问杜自芳:“她是谁?”
一阵悲凉从心底深处涌起。我的父亲连我是谁都不知道,我的母亲却时时刻刻都想着教训我。我有母亲,也有父亲,却还不如那些没有的人。
不等杜自芳答话,我一把推开他,跑了。
六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笼罩着整个京城,空气里一丝微风也无,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在热闹的街头毫无目的地闲逛,在各式各样的小摊前流连,京城毕竟是皇城,多姿多彩的路边摊把大街点缀得斑斓纷繁。有卖风筝的,手艺人坐在一堆竹篾彩纸中间双手翻飞,没多久就做出一个仙鹤式。有卖首饰的,玉器银器金器,簪花镯子花扣,五彩缤纷,耀眼夺目。还有卖绣花鞋、胭脂、彩衣的……
天气闷热难耐,云层渐厚,似有一场大雨在路上。我眯着眼睛看天,热得浑身没劲儿。
“姑娘,你要不要买?胭脂都被你捏烂了。”
我回过神来,才发现手上沾了水红色的胭脂,手里捏着的软盒歪了,洒了好些出来。
“我没钱,拿什么买啊。”我放回去,大声道。
小贩很不满,“什么人呐”。
我气哼哼地转过身来便看见对面的油纸伞摊,绚烂多彩的油纸伞高高挂着,像一片片五颜六色的云朵。
‘油纸伞中凝怨黛,丁香花下湿清眸’我来到伞摊前,取下那把画着牛郎织女的红色伞,浓浓的桐油味和着颜料味,让人嗅出崭新和技巧来。伞面上的牛郎手持砍刀,背着竹篮,织女却面坐绣台,手执细针,回过头巧笑倩兮地目送牛郎出门,二人目光动情,秋波互传,栩栩如生。这和常见的鹊桥相会大不相同,应该是他们会面之后的场景吧,很幸福。
摊贩大笑:“姑娘,你说的这些我也不懂,我是照着画样做出来的。”
我想买下,却身无分文。
“姑娘,买一把吧。这可是用上好的凤尾竹做成的,伞面不仅用湖纸,还加了一层棉纸,拿来遮雪都绰绰有余。”
我抱着伞:“可是我没钱。”
摊贩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姑娘,你开什么玩笑。”说着就要上前来拿回伞。
就在这时,不远处的城门外锣鼓震天,人声鼎沸,周围的人都开始朝城门跑去。
我也想去看看,却放不下手中的油纸伞。小摊贩瞪着我,我也瞪着他。
“姑娘,你既然没钱,还买什么东西呀。”
我不吭声。
他叹口气:“真是倒霉。天天摆擂,生意本来就淡了。还碰上你这么奇怪的人。”
“摆擂?”
“是啊。”
“干嘛的?”
“赛马。”
我眼珠一转,笑起来,“我现在就去拿钱来买。”
待我跑出城门后才发现还真是赛马,用人山人海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人群把城墙边上一个长度约五里的赛马场围了起来。那里是片沙地,原本是空着的,摆了一张神仙桌,供来往行人供奉,时常有些小孩子在这儿玩耍打闹。现在却支着一个擂台,擂台旁拴着很多马。
一个满脸胡须的壮汉穿着大红色的短褂,骑在一匹马上大声吆喝请战。
“听说他以前是帮南方的官府人家养马的,不止懂马的脾性,还深谙驾驭之道,来京城个把月了,还没碰上过对手呢。”
“莫非这人就是那个胡马儿?”
“就是就是,他爱马痴马,到最后都没人记得他的真名了,就叫他个胡马儿。”
“哪里才是京城,我听说他一路从济南过来,每到一处都设擂,还没输过呢。倒是赢了满堂彩,口袋里的银子都渗出来了。”
“哪里渗出来了?我怎么看不见……”
“哈哈……”
我听着旁边几个人无聊的对话,不由得翻翻白眼,深谙驾驭之道?他们难道没听说过本公主可是和硕特部的‘行踏落花不留香’?
“都说京城人才辈出,本大爷来了个把月了,既没见到虎头,也没见到狮尾。难道要让大爷我失望而归吗?有本事的、有胆量的,都出来试一试吧!只要赢过我,这锭金子就归他!输了也不怕,花三两银子买个乐,也不亏啊。”他三两句话就把底下的人说的挽袖束发,跃跃欲试。
这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我没有三两银子,连参赛的资格都没有。
“我来试试。”东边传来一记很平静的声音,却让所有叽叽喳喳的人住了声看过去。
大家却失望了,声音的主人儒雅年轻,一身白衣,长相俊朗,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深邃明亮,鼻梁高挺,嘴唇细薄,墨黑色的头发一尘不染,系着淡青色的发带。这更像是哪个大户人家出来散步的公子,哪像个赢得了大汉的壮士呢?人群不免发出一阵失望的哗然。
我却觉得他有些眼熟,像是在哪里见过。
“可以,公子一身侠气,准得让大家看场好戏。”胡马儿大声说道,眼角眉梢都有喜意,自觉已胜券在握了。
那白衣人虽然儒雅,却颇有些气势,压根不理会人群的喧哗,径直走到拴马的地方挑了很久,挑中一匹已有些年岁的老黑马,他娴熟地翻身上马,远远的扔了一锭银子到擂台的托盘里,正好打翻了里面放着的那锭金子:“开始吧。”
那锭银子足足有十两!真是奢侈。
少年挥鞭而出的瞬间就让众人大吃一惊,从他一气呵成的动作,行云流水的挥鞭催马,比赛结果便已毫无悬念。
我看得有些失神,这人的骑马动作同阿扎勒很像,想不到京城也有这般人物,竟可与在马背上长大的藏原人媲美。
白衣人赢得很漂亮,足足超过胡马儿一个马身。
胡马儿虽为商人,但也愿赌服输,很有气量地笑道:“我输了,公子年轻有为,我技不如人,还请留下姓名。”
那位白衣人坐在马上微微一笑,“大家萍水相逢,一个名字又何足挂齿呢。”
胡马儿哈哈大笑:“正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我老胡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在乎虚名的人!”
那位公子拍了拍骑着的黑马,笑眯眯道:“多谢”。
“那这金子?”
白衣人摆摆手,漫不经心道:“金子归你,我要这匹马。”
胡马儿一愣,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不行,我从不**。”
“这是一匹已近暮年的老马,根本不值得那锭金子,这是一笔不亏本的买卖。”
“千金难买,我的马是我的命,是我的福彩,赛马人从不卖马。”
“那么这样如何?”白衣人指着人群最前面,他的仆从拉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我们再比一次,如果你能赢我,那匹马就归你,这匹马我也不要,如果你输了,两匹马我都带走,这不叫卖马,这是伯乐识马,马认伯乐,很公平。”
白色骏马个头稍小,长长的鬃毛油亮顺滑,高昂着骄傲的头颅,全身雪白,无一丝杂色,不止肌肉健壮,连一双耳朵都竖直挺立,镶着金边的大红马鞍将它凸显得更加雪白,它的颈上挂着一颗银色的铃铛,有茶杯那么大,身动铃响,步步清脆,这是一匹好马,一匹上好的大宛马。难怪胡马儿的眼睛都红透了:“这……”
冲着这匹马,无论如何他都想赌一把,却又忌惮白衣人的骑术,所以犹豫不决。
“我来。”我大声道,这可是一个好机会。
这回所有人都看着我,他们只呆了一瞬便爆笑出声。
我疑惑地看着他们,又看了看我自己,没什么奇怪的啊,干嘛这么好笑。
尤其胡马儿笑得大声:“小姑娘别闹,快回去喝奶吧。”
那白衣人倒是挑眉看着我,嘴角很玩味。
我直接走到雪白的大宛马身边,从少年仆从手中接过缰绳,爬了上去,大宛马嘶叫一声,前腿扬起很高,我伸出手轻轻地在大宛马耳边抚了一把,他顷刻间便乖了。
我吆喝一声,骑着大宛马来到白衣人身边,一手指着胡马儿:“我替他比,如果我赢了,两匹马都归他,你刚才赢的那锭金子归我。”
白衣人看着我,像是看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他眼波流转,好一会儿才轻声说道:“我不跟女人比。”
“女人怎么了?”我气道:“是不是怕了?”
胡马儿痛苦地呻吟道:“小姑奶奶,我可没让你替我比,你别糟蹋了我的马。”
白衣人‘噗嗤’就笑了,我这才看见他脸上有风尘仆仆的疲累。
“他的赌注是黑马,你拿什么押注呢?”
我挽起袖子,“我。”
他哈哈大笑:“我要你干什么?”
我想了一想,“我可以帮你当管家。”杜自芳小老头会做的事,我也会。
“我不缺管家。”
“你怎么那么哆嗦,放心吧,你不会赢的,还是好好担心你的大宛马吧。”我狡黠一笑。
他沉吟半晌,“你凭什么认为你会赢?”
“你骑马时只顾驾驭马跟着你走,但不懂得迎合马儿的脾气,你一味地想去赢,马儿却不想,所以你输定了。”
他哑然失笑,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你一个小姑娘,竟然懂马?只怕整个京城也没人敢指责我的骑术。”
我伸出手来比了半指的长度,“你差阿扎勒只那么一点点,不相信的话比了就知道。”
“阿扎勒?”他不明所以。
依旧是鼓角齐鸣,锣声震天,人聚得越来越多,都抱着看马戏的心态簇拥嬉闹。
胡马儿战战兢兢,站在我的马前捶胸顿足。
雷声轰鸣,雨点如豆,我仰头望着阴沉沉的天空,一场大雨正在路上。
随着火炮打响,大宛马很配合地扬起前腿,狠狠地嘶叫一声,飞奔而出。
好在我今儿穿的是简单的藏族服饰,束腰短褂,亚麻长裙,鹿皮靴子,比较适合骑马。
我的骑术是阿尼手把手教的,他把年轻时驰骋沙场那套本领毫无保留地全部教给了我,有时候连阿扎勒都憨厚地向我讨教,可我就是说不上来诀窍在哪里,仿佛只要一坐上马背,就如鱼得水起来,策马奔腾靠的不是好马尖刺,而是懂得马的心思。
我平生不学无术,学什么都坚持不到底,只有两样东西坚持下来了并且很厉害,一个是射箭,一个是骑马,要怪只能怪这公子运气不好,偏偏被我碰到,偏偏我还很缺那点钱。
雨越下越大,围观的人群屏住呼吸,纷纷撑起了油纸伞,没有带伞的拉起衣袍遮雨,都不愿离去,想亲眼看看这场“力量悬殊”的比赛结果。
我之所以这么有信心,首先是因为大宛马比他骑的那匹上了年纪的老黑马好得太多,这样一来,我只要不分心就行了。因为雨太大,赛场中间有一段被雨水冲得陷了下去,白衣人本能地进行避让,这让我不免有些吃惊,他这么想赢,却在紧要关头进行避让?我见陷坑虽小,却很容易让马儿失蹄摔倒,但我不甘心就这样绕过去,我见陷坑旁边有一块沾满了污泥的小石头,便下了决心,收起马鞭,往右狠拉了一下缰绳,马儿左蹄飞往右边,在过陷坑的一瞬间,右蹄不偏不倚正好踏在小石之上飞腾而过,周围忽地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欢呼,我在心底暗笑,这回还不赢你?
我捧着金子的时候胡马儿正抱着大宛马的脖子笑得欢畅。白衣人虽败却无悔色,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已被胡马儿拉进圈栏里的老黑马,浑身上下早已被大雨淋得湿透了,一缕雨丝顺着他黝黑的发尾滴落,在他身后的地面上形成一个与众不同的小漩涡。
我擦擦脸上的雨水,见他这般模样,觉得有些过意不去。
“你损失了一匹大宛马,要不这锭金子分你一半。”我蹭过去。
他笑了,“愿赌服输。”
“那我请你喝酒?”我拉拉身上湿透的衣服,一件件地黏在身上好不舒服。
他打量着我的衣着:“你是哪儿的人?我没见过骑术这么好的女孩子。”
他的仆从从远处跑来,手里拿着一把伞,急切地撑在他头上:“爷,看着雨势不会小,本就病着,赶紧回去吧。”
他还病着?我佩服地点点头,心思略一动,便三步并作两步跑到胡马儿那儿要回了大宛马颈上那颗铃铛递给他:“既然你病着,喝酒的事就算了,下次见到再请你吧,这里可是有你的一份。”我朝他挥挥手里被雨浇湿了的那锭金子,“这颗大铃铛权当给你做个纪念,免得你太过思念大宛马,夜不成寐。”说完‘哈哈’一笑,只因心里惦记着油纸伞,不等他说话就先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