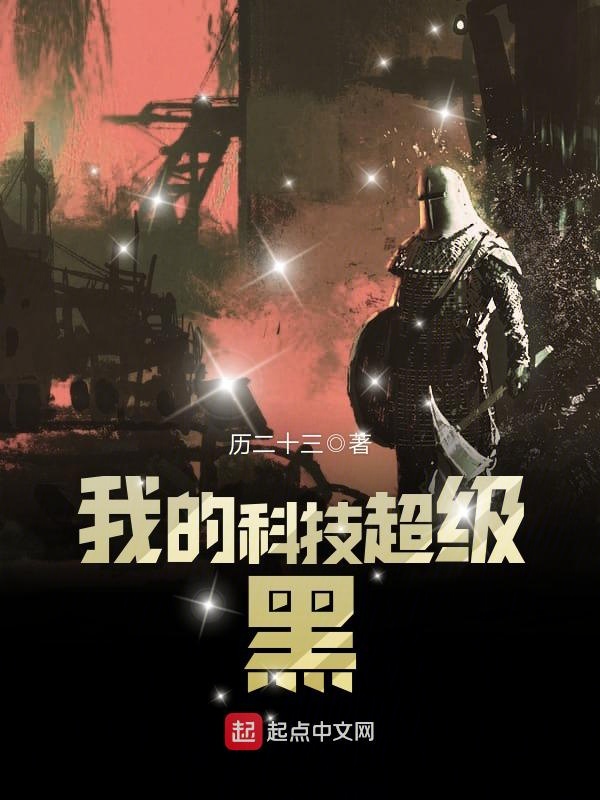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奥洛尔年代记之日轮低语》终章 君权与共和 免费试读
常有人说,那弗伦索西亚的伦培尔陛下,不像是一位皇帝。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跑到军营,观摩指导军队的晨训。然后七点到城中的酒馆吃早饭,就着酸葡萄酱啃上半只鸭子加上两块**包。在城里的各个部门溜达一圈之后,十一点左右回到他位于青金宫内的办公室,也不知在忙些什么。用过午饭后,在午睡的时间去自己姐姐,罗兰菲尔公主殿下的办公室,两人换好衣服之后,会去附近的皇家猎场打两只随便什么动物,然后下午五点回来,和约见他的客人们一起用晚宴。这皇帝的一天,完全不像是一位统治三个王国的皇帝,倒像是个工作比较闲的小事务官。
而今天一大早,他没有选择去军营或是城市中,这位皇帝在两名骑兵的护卫下,来到了郊外一家不大的小农庄。
伦培尔把马停到农庄的大铁门门口,翻身下马,把缰绳交给自己的随从,然后凑到门口,看到园中有一个园丁,他大声问道“您好,请问这是阿库耶尔老人的家么?”
园丁并没有看他,继续用园艺剪修剪着灌木丛“是,您哪位啊,他老人家不见客。”
“我是伦培尔.佩兰,南境帝国的正统皇帝。”
“我还是约翰.史密斯,阿库耶尔大人的园丁呢,滚滚滚。”那园丁也没好气的回复道。
“让他进来吧,”里面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园丁打开了门,穿着军装长外套的伦培尔推门而入,朝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
他绕过了几个灌木丛,终于,看到坐在了大躺椅上的老人,那个行将就木,如同一捆柴火的干瘪的老人。
“您终于肯见我了是么?”
伦培尔坐到那枯槁老人的对面的一块大石头上,把自己的仪仗剑横在膝盖上。
那老人看着面前的伦培尔,又拉动了一下膝盖上的毛毯“我最近,经常梦到黑色的鸦车,恐怕已经没有几个日子可活了,总不能直到我死,都不见您一面。”
“那就好,我一直在想,您总不至于从五年前一直病到现在。”伦培尔微微笑着,旁边的侍女推过来了一个小车,上面摆着酒桶和清凉饮料桶。
伦培尔自己倒了一杯清凉饮料“老人家,你喝点什么?”
“松子酒,谢谢。”
他接过伦培尔的酒杯,笑着,露出了他一口多少有些发黄的牙“让一位执政官给我斟酒,是我的荣幸。”
“希望您老还没糊涂吧,”伦培尔喝了口清凉饮料“我现在是皇帝。”
“哦?来访时,我记得您说您是伦培尔.佩兰,”阿库耶尔喝了口那澄澈的褐色松子酒,辣的咳了几声“可我记得,那是弗伦索西亚最后一位执政官的名字。”
“老人家,您糊涂了,他五年前,就成了整个南境的皇帝了。”伦培尔笑着说道。
阿库耶尔板起了脸,笑意全无,他在自己的眉前挥挥手,似乎是想要驱走来索命的鬼魅一般“伦培尔,当他还是位执政官的时候,他还有这样一个名字,可是当他成为皇帝时,他便没有了名字,如果非要说的话,他的名字叫佩兰。”
伦培尔干巴巴的笑了一声“老人家,佩兰是伦培尔的姓啊。”
“不不不,皇帝,或者说类似的国王和公爵、伯爵,都是没有名字的,”阿库耶尔摆出一副给学生讲课的样子“他们的一切行为都为他们的家族延续,为他们的家族继续占有着一片土地上的利益而服务,你也是这样,佩兰。”
伦培尔没说话,他多少有些明白了老人的意思,但是还是无法认同。
阿库耶尔又喝了口酒“我曾经幻想着一个国家内,议会能够主掌大权,而国王只是议会中的一份子。但是后来,我发现,有一个暴君,他太过强大了,以至于那些勇者们想要毁灭他时,都无能为力。我很遗憾,我没有看到暴君的末日。”
“暴君?您是指那佩兰么?”伦培尔听到这些话,不怒反笑,手指轻轻地叩着旁边的石头。
阿库耶尔摇摇头“佩兰?不不不,他还算不上暴君。真正的暴君,是主导了那本名为历史的书,延续了几千年的无知和蒙昧。”
“无知和蒙昧?”
“是的,自古以来,有着无数的君主,他们是主导着历史的人,”阿库耶尔顿了一下“他们能够主宰整个人类的历史,原因嘛,无非就是人类,还依旧愚蠢,依旧蒙昧无知。我问问您,您觉得,为什么人们要有一位君主?君主于人,有什么好处?”
伦培尔看着老人那浑浊的眼睛,他不确定阿库耶尔是否还能看见他,于是先喝了口饮料“人们懒惰无能,所以需要君主的勤奋去驱动他们;人们保守落后,所以需要君主的智慧去启迪他们;人们奸诈狡猾,所以需要君主的热诚去肃正他们。君主用自己的美德,去让那些贫者升华。去用美德荡清贫者的罪恶。”
“呵,陛下,瞧瞧您说的,贫者的罪恶,”阿库耶尔露出了副格外瘆人的讽刺表情“他们何罪之有?他们受着由祖辈而来的贫穷,因这贫穷,他们不会识字,所以奸诈狡猾;因这贫穷,他们不知时事,所以保守落后;因这贫穷,他们努力而不得财富,所以懒惰无能。”
阿库耶尔放下酒杯,敲了敲椅子的把手“他们一切的罪恶,都源于他们的贫穷,正如您所有的美德都源于您的富有一样。为何您占有您天生的财富就成了美德?为何他们留着他们天生的贫穷就成了罪恶?”
“陛下,佩兰陛下,当我们讨论愚昧和无知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阿库耶尔向前探着身子,几乎凑到伦培尔脸上“我们在讨论识字与否?读过多少书么?不是吧,我们在讨论的,是人所相信的东西。当一个人相信大地是一块平板的时候,当我们到了海洋的边缘,就会坠入巨大且深不见底的瀑布,我们说这个人,是愚蠢的。而相信王权,也是一种愚蠢,一种堪比真的相信太阳是一匹黄金做的马一样的愚蠢。”
“呵,您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世上有造福黎民的圣罗叶德,也有长治久安的四贤人,还有那维系和平的卡洛斯四世,就算我们讨论南境,也有我的母亲和太祖父,让整个弗伦索西亚从内战的消耗中恢复过来。您觉得,这些人是愚蠢的吗?”
“不,我还没有那个胆量,”阿库耶尔大声道“这些人的功绩,足以让他们享有死前与死后的盛赞,但是这真的是给他们的孩子同等的权力的理由么?优秀的父亲就一定有优秀的孩子么?”
“不是,那是当然的。”
“您所说的贤君们,在历史上固然是存在的,”他右胳膊拄着椅子把手,撑着脑袋,而左手则轻轻捻着自己那花白的胡须“但是那暴君,存在的数量,似乎远比那贤君多上百倍千倍,而他们,只会受到死前与死后的指责和怒骂,他荼毒他所统治范围内的百姓,但是却可以不受到任何处罚地安静地死去,请问这是不是一种愚昧呢?”
“您说的对。”伦培尔低下头。
阿库耶尔突然的喘气声突然重了起来,而过了十几秒,又恢复了正常“宽恕我的不敬。陛下,老年人的气管总是像破了的风箱。这样吧,陛下,我们来拿你做个例子,你用你生命中的前二十年统一了整个南境,不算布里托尼亚的话,就假设您能活到。。。您今年贵庚?”
“二十三。”
“好,那就假设您能活到六十,到那时,想必这个帝国疆土稳固,承平日久。而您的孩子将继承您的帝位,若这孩子,是个独一无二的暴君、昏君、庸君,那会发生什么?”
“南境的人民反抗他。”
“是的,南境的人民会反抗他,而南境的人民在反抗时,面前就会有一堵高墙,那就是您一手建立起的军队。也就是说,那样一位暴君、昏君、庸君,在拥有您的军队的情况下,会仍然稳稳地坐在皇位之上。”阿库耶尔微微笑着“这就是君主制的愚蠢。拥立您做皇帝的人那浅薄的思想不难理解,他们认为这样的功绩只有皇帝这样的头衔才配得起,而事实上,他们是将百年后的自己,推进火坑罢了。”
“我们大可以完善制度,让那样一位暴君昏君庸君无用武之地。”
“呵,年轻人,你太过天真了,”阿库耶尔用一只手轻轻地捏着自己的手臂“一项能够限制暴君的制度,一样可以限制一位贤君。说到底,什么是暴君,什么又是贤君呢?”
伦培尔愣住了,他稍微想了想,似乎阿库耶尔所说不无道理。
“陛下,我并不是要说服你,但是你已经从人民的伦培尔变成了帝国的佩兰,当你仍是一名执政官时,人们可以以你的过失弹劾你,国民大会可以因你的无能罢免你。可现在呢?指出你过失的人,需要遣词酌句的‘劝谏’您,而国民大会,呵,则彻底变成了您的顾问团,一个趋炎附势的空架子。”
伦培尔什么也没说,他看着阿库耶尔,这个老人。君主制是愚蠢的,这是他从头到尾说出的话中,唯一的主题。给予一个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力,或许这个家族的兴盛能够维持十年,二十年,可是再往后呢?再往后,这个家族真的不会从帝国的大脑,变成帝国的吸血虫么?
阿库耶尔的笑脸咧得大大的,他看着伦培尔,看着那紧紧纠结在一起的眉毛,喝了口酒“陛下,您在思考,这是好事。但是你的思考,大抵是全然无用的,因为您死后,还有您的儿子,您的孙子。就算您能活到百岁那样的长寿,您也顶多就能看见您的儿子掌权吧,而您孙子,儿子的孙子,孙子的孙子,会把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则完全不是您所能看到的。人的生命,满打满算也不到一百,又何必顾虑千年后,人们的忧愁呢?”
“所以,你刚刚跟我说的这些,只是为了搅乱我的思绪,让我忧愁是么?”伦培尔苦笑着,喝了口那清凉饮料,橘子汁的酸味和薄荷的苦味让他似乎感受到了忧愁的味道。
“哈哈哈,陛下,您说笑了,”阿库耶尔咳嗽了两下,气息也变得微弱起来“我在五十五岁时,接触了共和的理论,然后便开始因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忧烦,如果国王回来了,该怎么办?后来,我坚持宪法君主制,我相信宪法和国民议会能够限制王权,但是事实告诉我,我错了。当我六十二岁,不再做财务总管的时候,我在想,我究竟为的是什么?我没有孩子,也没有产业,仅仅是凭着对一群人,对这片土地的爱,去完善法律,去与君主对抗,去和共和派辩驳,有什么用么?没有。只要两个精明干练的王室的孩子,就能粉碎我想过的一切手段。那我的思绪又有什么意义?我当初,就不该让您假退位,而是应该将你彻底架空,才对。弄巧成拙啊。。。”
两个人又陷入了沉默,空气中,只有园艺剪修理灌木的声音。
风轻轻地吹着老人的头发,似乎这个老人的生命,正在肉眼可见的慢慢流逝,他看着伦培尔,而伦培尔总想要说些什么,却每次话到嘴边,都没有说出来。
“您走吧,陛下,”那老人的气息越来越微弱“我这样的人,不配占用您这么长的时间。”
伦培尔起身,看着他,走出几步,又回头看着这位老人,仿佛这是一个标记,一个时代的标记一样,就像瑞奇尔德王城是古典时代的标记,而紫山堡垒群是中古时代的标记一样,这个老人似乎宣告着某个时代,某种浪潮的结束。
他又走出几步,但是那老人却如同吸铁石一样吸引着他的目光。
“阁下,我想最后问您一件事,”他看着那枯槁的老人愈发的与那躺椅融为一体,听到他的话却用胳膊撑起了自己的身躯,他便说道“阁下,我究竟是否应该忧心这国家的未来?”
老人摆摆手“不用,忧心未来,是开拓时代的人的事情,那,可比做一位帝王,难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