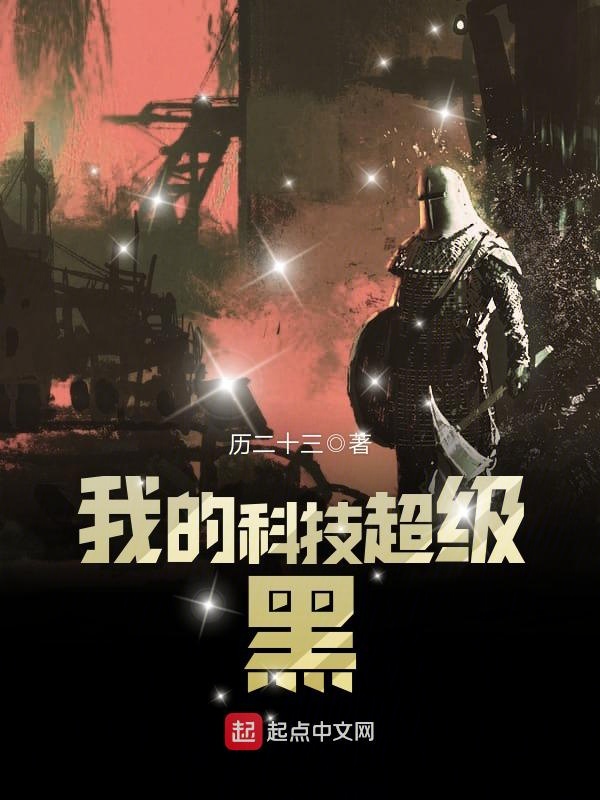《少年从风下山记》第十一章 鬼风疙瘩 免费试读
从风虽然有力气,但不习惯干扛大个的活儿,郧中隐只求他不瞎跑就落心了,因此让他和庚妹在一旁闲坐。
曹嘎三瞅着两人待一块,心里拈酸吃醋。趁个间隙,买一串糖葫芦送到庚妹面前,讨好说:“庚妹,给你的。”
庚妹急忙接了,说声:“谢谢嘎三哥。”
曹嘎三见她笑意甜甜,自己也跟着眉飞色悦。岂料转身没走出几步,一回头,庚妹竟掰着喂给从风吃。
从风只顾自己喜欢,也不懂得相让,一手捞过来,横咬竖舔没个吃相。
曹嘎三顿生厌恶,趋步近前,讥讽说:“俩肩膀扛张嘴,还饕口馋舌。”
从风听不懂这话的意思,满眼疑惑望着他。
庚妹听曹嘎三说话忒刺耳,因之前对他逼着从风搬开憋气,这会儿要借机给他脸色看,一把夺下从风手里的糖葫芦摔在地上,不屑说:“走,我们自己去买。”
曹嘎三气不是,恼不是,只好闷声去干活。
庚妹领着从风走到卖吃食的货摊前,迎面撞见来喜和二黑,叫住二人,说:“你俩谁请我们吃糖葫芦。”
来喜说:“我正找你呢,开边说句话。”
庚妹站着不动,说:“你先买糖葫芦。”
来喜只好去买了两串糖葫芦来,庚妹都塞给从风,交代他不要走开,又嘱咐二黑陪着他,才随来喜避开人到别处说话。
来喜忙着往内衣口袋里摸。
庚妹怕从风走散,催促说:“啥事儿,快说。”
来喜掏出一个密封的信封,说:“师父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庚妹拆开,抽出信瓤儿展开一瞅,顿时瞠目结舌,脸色都变了。
来喜瞅她不自在,猜是师父对她不满,凑过来要看。
庚妹惊慌失措,又不敢扔地上,遂忙把信瓤儿揉成一团塞嘴里,吞入肚中。
来喜惊惑不已,问道:“师父说啥了?”
庚妹支支吾吾,但瞬间藏惊敛愕,淡淡的说:“没啥要紧事儿。”
转身回来,瞅见从风嘴边沾着糖腻子,跟个孩子似的,心里涌出些许酸楚。她现在似乎知道了一点师父的心思,惊叹师父的贼眼好厉害,不知不觉把从风身上的东西看到了。她希望师父就在这件事上打止,不要再玩别的幺蛾子。她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照师父的话去做,要是做了,可就更加对不住从风,要是不做,又怕师父起谋害之心,心里倍儿纠结。
从风舔嘴咂舌,美滋滋的说:“两根我都吃了。”
庚妹定了神思,把笑容挂上脸,问从风:“还吃吗?”
“吃啊,挺好吃的。”
庚妹又去买了两根,这回从风只接了一根,推让说:“你自己也吃,你还没吃的。”
庚妹想起曹嘎三说他“饕口馋舌”,问他:“你知道嘎三哥刚说你什么吗?”
“什么?”
“说你馋猫儿,不会干活只能吃闲饭。”
“他这么说我?”
“不过呢,话粗理不糙。中隐大哥让你留下来,马大哥又给你找了一处房子,吃饭要钱,租房要钱,也不能让人家白养着你。要我说,你扛不了大个,还是耍些小把戏,多少也能赚几个子儿。”
“成。还跟咱俩来天津路上那样,你给我当帮手。”
二人说定,当下去店铺买了几样能做道具的物件,庚妹还买了一面小锣,再回到码头,选一处人来人往的地儿,做起卖艺的营生来。
天津卫的杂耍戏法与曲艺一样盛行,撂地的并不鲜见。这二人的做派虽说差些道儿,但从风玩的小玩意儿极见功夫,仿学禽畜鸣叫更是令人难辨真假,加上他憨呆得滑稽,竟有不少看客情愿捧场。半晌下来,赚的铜板远比扛大个多。
到了傍晚收工回去,从风定要出钱做东,大家图他高兴,遂了他的愿。席间个个夸奖,从风喜不自胜,自称:“回头赚的更多,租房的钱,我自己付,翼飞大哥的也归我付。”
果然次日起来,他又叫着庚妹去撂地。一天下来,顺心随意,兴致如昨。
庚妹慰劳他,又去买了四串糖葫芦。
大家以为他忘了要去茶楼的事儿,都在暗中高兴。岂料黄昏时分,他收拾完摊子,举目之间,瞥见一个人影,像是邱持贵,把手中的东西塞给庚妹,拔腿去追。庚妹瞅他神急意促,晓得有事,慌忙跟上去。
码头上人头攒动,邱持贵花一眼就没了影儿。庚妹上前揪住他,忙问:“干什么呢?”
从风像丢了魂似的愣站着,眼巴巴望着人潮,眼神失望而木然。直到收工回去,一路闷闷不乐。谁跟他说话都不肯多言,吃饭时只顾低头喝闷酒。
吃罢晚饭,大家陪他一块坐着闲聊。
“好痒。”从风忽然嚷一声,两只手在身上四处乱抓乱扰。随之眼皮、脸颊和脖颈,一块一块的红肿起来。
郧中隐叫一声:“鬼风疙瘩——快叫郎中。”
马翼飞摆手说:“别慌,先用土办法,从风你忍一忍。”
马翼飞跑回原先的房间,从床底下拿出一包银丹草过来,用开水润湿后替从风擦拭,全念坤过来打帮手。岂料擦着擦着,从风身子一歪,倒在全念坤身上。
郧中隐说:“睡着了?”
众人急忙把他架到床上。
马翼飞说:“睡着好,睡着了就不痒了。这玩意儿来得快去得也快。”
庚妹说:“马大哥你这是啥灵丹妙药?告诉我,下回我要遇上了,好自己对付。”
马翼飞说:“我也爱患这毛病,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就是薄荷叶,郎中开方写作银丹草。”
当下各自回去歇息,一夜无话。
次日早起,兄长们都过来瞧他,从风睡着还没醒。
郧中隐对大家说:“别叫醒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大家吃罢早饭回来,从风还在沉睡。因天又下雨,不好干活,四大棍便在老孙头家推牌九赌钱,让庚妹照看从风。
庚妹替他们四个泡好茶,在牌桌前略站了一会儿,觑着他们聚精凝神,便转身往从风房中来。
她望一眼从风,仍然睡得很沉,动起了心眼儿:前天师父让来喜带来的信中说,从风身上有件宝物,命她盗到手。她从未见过从风身上有什么宝物,心想能上师父的法眼,一准儿老值钱了,我趁这会儿工夫,瞧瞧究竟是什么玩意儿。于是伸手往从风身上摸,可她的手刚触到从风的身子,一个冷颤把自己打成了冰碴儿,顿时胆破心裂,禁不住尖叫起来。
四大棍闻声,不知出了什么事儿,丢下牌,慌忙跑进来询问。
庚妹泣道:“从风不知怎的了,身子都凉了。”
郧中隐伸手一摸,果然一身冰凉,惊魂惊魄说:“老马,坏了,人没了,这是咋回事?”
大家都伸手去摸,马翼飞把人挡开,探了探他鼻息和脉搏,说:“还有气,念坤,快请郎中。”
“一句话的事儿。”全念坤飞跑出门。
马翼飞拿热毛巾往从风肚脐和额头上敷贴,又给他加盖了一床棉被。大家聚坐房中焦急**。
不出一个时辰,骨瘦如柴的萧老郎中骑一匹驴过来,诊了半天脉,竟皱眉不语。
郧中隐性躁,忍不住说:“我说郎中,您别跟没嘴儿葫芦似的,能治不能治,开开尊口,不行咱就请别人,别耽误了病人。”
萧老郎中没在意郧中隐,一眼瞅见盆里泡着的银丹草,抓一把闻了闻,问道:“这干什么用?”
马翼飞把昨儿晚饭后发生的事儿告诉他。
萧老郎中又问:“昨儿晚饭吃了什么?”
马翼飞又把晚饭所吃一一告知。
郧中隐耐不住性子:“老问些没用的,到底人有不有救!”
萧老郎中还是问:“日间吃了什么。”
庚妹抢先回答:“中午吃馍、咸菜。还有,这两天吃了好几个糖葫芦。”
萧老郎中命人把银丹草端出去,慢条斯理说:“这位小哥儿也不算是病,身子无大碍,无需下方。给他洗个热水澡,把被褥换了,也不用盖恁么厚实,睡个一天半晚自然会醒来。”
郧中隐忙说:“你有不有把握?可别坑人!”
萧老郎中瞥他一眼:“性命攸关,岂敢戏言。”
郧中隐说:“你敢戏言,咱哥几个的拳头可不是吃素的。你倒是说说,到底咋回事?”
萧老郎中说:“此人体性殊异,对银丹草气味不适。如此怪异症状,老朽行医数十年,只见过两例。此类人与银丹草相斥,只要触及就会晕倒,但不用一炷香的工夫即可复元。这位小哥儿想必之前睡眠不足,或者劳累过度,所用药物剂量过大,以致深度昏迷。日后要避免接触银丹草,便是银丹草的气味也不能闻。至于鬼风疙瘩,恐与糖葫芦有关,也有人不宜多吃。”
大家听他说的有些道理,稍稍心宽。
郧中隐说:“没你事了,你走吧。念坤,给他几个子儿做出诊费。”
全念坤扶他起来,把他送至门外。
庚妹烧了一锅水,郧中隐和马翼飞替从风洗了澡,又把被褥换了个底儿掉。马翼飞只道是自己害了他,心中愧疚,让庚妹去推牌九,自己寸步不离在床前守候。
外面推牌九的四个毕竟静不下心来,赌了一轮便散了,各自无趣。
老孙头正劈柴,嗷嗷如牛喘,郧中隐瞅他不利落急眼,推他到一边,夺过斧头一劈两半两劈四开替他代劳。
全念坤眼力见儿,帮他把劈柴搬去屋后堆垒。脑袋磕碰到檐边,回望一眼,说:“老孙头,你这样差道儿,可不容易着火吗?”
老孙头不以为事,回答说:“我厨屋不在这边,哪儿来的火。”
全念坤说:“一句话的事儿。”